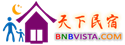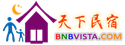|

终于赶在朋友去西藏前一天,把文字放上来了,谨以此文献给6.29日和我一起赴藏的亲爱的团友们!
去程,北京来的小雪从早上登机,直到晚8点半才踏进和我同住的房间。飞机中途经停延误,说是三小时的飞行,小雪折腾了一整天在路上。
回程,团里已入美国籍的大连妈妈快赶上飞美国了。拉萨到大连经停徐州,因天气原因,飞机到大连后无法降落又折回徐州,娘仨干脆在徐州又被拉去了一日游,第三天才抵达大连。
西藏好远。
在许多人心中,这个离天最近的地方不光路途遥远,更遥远的是心理距离:世界屋脊,稀薄的氧气,变化多端的气候,长途跋涉……每个人经受的不光是地理意义上的海拔,更是生理和意志上的新高程。


这就是西藏,一个让内地人向往而生畏的地方。有人说,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西藏梦。
带着同样的梦,在朋友们的羡慕嫉妒恨和嘱咐声中我报名“游侠客”,成了一名进藏者。回程后,和临行前一样,周围的人还是同样的感叹:“我也好想去西藏!”
为什么不去呢?人生一辈子,连十来天的时间也抽不出来,去一个自己心仪已久的地方?
其实,这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神秘,也没有鲜花满地,甚至面对佛主时,我除了敬畏而鲜有神圣感从心中升起,但西藏十日,让我在一个极度矛盾对立的世界里,尽情享受着自由短暂放飞的感觉。
在布达拉宫、大昭寺,导游阿旺讲解得口沫四溅,面对磕着长头的虔诚百姓,我依然一片茫然。只有当我们一行人行驶在去林芝的路上,徜徉在雅鲁藏布江支流尼洋河边时,半山腰慵懒的云朵唤醒了我。我突然发现,西藏和内地是多么的不同!
一边是让人千里迢迢奔来顶礼膜拜的神的召唤,一边却是世外桃源般的潇洒自如和放荡不羁。在哪里去找这么极端的二重世界?蜿蜒的尼洋河一路伴随着我们,这里没有崇山峻岭,没有激流澎湃,有的只有静谧和安详。河流在打盹,连天空也在发呆。山下的树仿佛伸了个懒腰,一蹬腿把自己像苔藓一样铺到了半山腰。
车上的我们只能算一群不速之客,闯入了这个灵异山谷,却又冥冥之中走在同一条路上,翻动着各自心中的经幡。
都是灵魂,为何一个被束缚在崇拜的殿堂上,一个却随意驻足。其实造物主的安排莫不浑然天成:没有约束和规矩,哪来这慷慨赐予的灿烂阳光和天高云淡?

在西藏,极端的事还远不止这些。就拿天气来说吧,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一早拉开窗帘,金蕃饭店外的街道湿漉漉,寒风习习,街上裹着长袍的藏民们脚步疾促。我瞬间放弃了要穿着长裙去布达拉宫拍照的幼稚想法。最御寒的,不就是那件套头的抓绒衣吗?
这下好了,在拉萨厨房用过午饭后,前往大昭寺的路上,那才叫热啊!虽然穿的是厚长袖,但手臂明显感觉到持续炙烤的刺痛。阳光,从3万英尺以上的高度毫无遮拦的倾泻下来,洒在我们身上每一个裸露的角落。
看着我们忙不迭的涂防晒霜、戴帽子、围披风、蒙面罩,阿旺却一动不动。戴上墨镜的阿旺说:“我们什么也不涂。”
今年上半年,我去澳大利亚的最南端出差,那里的阳光和这里同样的热烈。但除了中国人,当地人几乎没人撑伞遮帽。当地留学生说,阿德莱德市是皮肤癌高发区。但澳洲人就觉得阳光是礼物,是大自然的馈赠,为何阻挡在伞下?
西藏给我们的“享受”总是极端。就在冷热交替中我先后患上热伤风、扁桃体发炎到受凉感冒,吃遍团友们送的药后,老天爷送来了纳木错。那天,水天一色。我才知道,我一路追逐的白云原来住在念青唐古拉山的尽头——纳木错湖的对岸,才是白云的家。


远处的纳木错浩瀚壮美。站在4000多米海拔的垭口,远眺高原上中国第二大咸水湖,这个角度望过去,像极了法国波尔多大沙丘濒临的大西洋一角。地形、沙丘、弯道,难道在梦中?还是地球上绝美的风景总是神似?


法国波尔多《将爱进行到底》电影拍摄处 摄于2011年10月
在我的眼中,纳木错是一个雄性的湖。狭长的沙滩,我原以为洁白柔软,没想到当我跪下时皮肤被咯得生疼,就像扎上了长满面颊的络腮胡。纳木错的水缓缓而清澈,水草浮动,但尝一口却是咸的:就像男人身上淌下的汗珠。他胸膛宽阔,热情洋溢、阳刚气十足。
相比之下,那个让人期待已久的羊错雍湖算是闭月羞花了。那是我们入藏天气最阴冷的一天。车行至传说中的羊湖,无奈寒气逼人,天茫茫,水茫茫。我们只能“在水一方”摆尽各种造型胡拍一通,回去后照片导上电脑,湖色浑浊,只剩我们张张好奇的脸。这次见到了真男儿,却无缘掀开美少女的面纱了。
在我看来,西藏给内地人展示的更多的是对形式的束缚,实质是让灵魂自由放飞。这里可能是中国安检最严格的地区。无论是进布达拉宫广场,还是游罗布宁卡行宫,层层过包检查。准确说,在我从成都登上去拉萨的飞机前就开始接受最严格的检查了。拉萨火车站,只有少数几趟火车,直达北京、上海、广州、西宁和重庆的往返等。这里晚上6:30就下班,下班后火车站除了值勤的军人,再无旁人。这是我见过最安静的火车站。
在旅游大巴过往之处,无数道关卡要过。无论来回,我们的身份证要重复接受检查。难怪来之前领队就说,如果来拉萨忘带身份证,那只能寸步难行。
然而,当你突破禁区,西藏会敞开怀抱接纳你,你恨不得化成天边的一朵云,草原上的一头羊。车在藏北草原行进时,远处的雪山、两侧的草原,阳光、牛羊、云彩一点点向我逼仄。此时的我,恨不得把大巴车变成四面进光的敞篷车,好让我从车窗外伸出一只手抓一把云彩,或者摘一朵雪莲。

天路1

天路2

天路3

天路4
无数次设想,如果司机随时可以把车停下,我跳下车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辽阔的草原上先打几个滚。
在车上曾问团友,如果上天给你一个选择,除了人你可以变成其他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你愿意选择什么?有人说想变成一只小鸟,可以自由飞翔。有人说,想变成一头猪,可以幸福到死。而我,只想变成一棵荒野里的树,虽历经风吹雨打、电闪雷鸣而屹立千年,可以在风中应和鸟鸣,任牛羊绕膝,和月光谈情,受日神沐浴,和光阴赛跑。
其实不光是西藏的天,西藏的佛,西藏的景让人目眩神迷,西藏当地人的欲念和内地也有着极大的反差。
阿旺是我近距离接触的第一个藏族人。从业10多年的他现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6岁的女儿,年迈的父母和他们三口一起生活在拉萨市新买的公寓里。除了房子,阿旺还有一个QQ开着上班.对现在的生活,阿旺很满足:”有房有车了,家里人也没什么花销。”
怎么能没什么花销呢?在内地的发达城市,那么多拼命挤地铁、挤公交的人,做梦都想买套房子或买部好车.有了房子的人还想换更大的房子,最好是别墅。有权势的人还想泡更多的妞、捞更大的官……

阿旺和女儿
阿旺还亲口告诉我,他和妻子甚至没有经过自由恋爱,是从小父母在日喀则农村就包办定下的。妻子没念过什么书,阿旺一直读到了大学。“但妻子很贤惠,每天都陪老人去转经。”阿旺很安心,正是由于有了妻子的打理,他才能在外面当导游挣钱养家。
大多数内地人都装有一个西藏梦,不管是回程列车上骑自行车从新疆到西藏拍到藏羚羊和野牦牛的青海油田工人,还是拼车从川藏线进藏的军人小伙子,还是带着刚研究生毕业的儿子进藏的长春妈妈。那么,西藏人的西藏梦是什么?
阿旺告诉我,他最大的梦想是能在拉萨市开一家藏餐厅,因为妻子喜欢做饭。“不过要30多万元呢,这些年钱都用来养家了。”他说,自己还要拼命努力,否则哪里挣得了这么多。
去内地发展呢?阿旺说,他只去过内地一两次,并不向往。因为那里没有这样的阳光、蓝天和白云,他并不习惯。
什么样的人,对繁华和未知不心动?
“我们有自己的信仰。”阿旺说。
信仰是什么?
在从拉萨到西宁的回程火车中,我一觉醒来,睡在我对面下铺的藏族妇女早就起来翻看经书,口里念念有词了。她念得很小声,怕惊扰了我们,那是一些黄色的纸片,上面写满了娟秀的藏文。
她是去青海看上大学的女儿。沿着青藏铁路去看望孩子,一直是她的梦想。
待她念完经后,下铺的长春阿姨把洗好的水果放在茶几上,递给她。没有常见的推辞和客气,她顺手接了一个还滴着水的新鲜油桃放进嘴里,笑容一下就荡开了。就像车窗外飘过的云,再自然不过。
车过青海湖,她在车箱尾部站着。我也端着相机在车箱前部,对着窗外。一扭头瞟见穿着深酱红色长袍、满脸高原红的她。快到西宁了,虽然没有一句话,但我们同时都笑了。
西藏人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十日太短,我没能找到答案。
在微信上,阿旺曾发了一个帖子。随着游客的增多,西藏的酒吧、会所、朗玛、歌城、**也多起来,但向全民开放的健身场所却少了。“如此喝下去,赌下去,沉迷下去,除了雄壮的身体和羞涩的钱囊,还有不和谐的家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了!”他疾呼。
不得不说,西藏依然是贫穷的,不论国家每年给了多大的支援。西藏发展靠什么?
“你看这是在挖铜矿。”从日喀则回拉萨的路上,阿旺指着路旁被劈开肚子的大山说:“西藏的经济发展要加快,但开发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在中国,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是一对无法避让的矛盾。不仅是西部的云南、青海、四川,这样的博弈也同样在青藏高原上演。有资料表明,三江并流源头已到了生态保护最脆弱的边缘。游客沿青藏铁路路过可可西里时,已很难再看到藏羚羊。前些年,屡禁不止的挖虫草已让高原草场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那么西藏发展旅游业如何?就我个人来说,这亟待深入挖掘。目前,西藏的旅游还是以观光和自助旅游为主,但休闲旅游的大门却未叩开。同处西部的云南已走在休闲旅游的前列,继传统观光线路“昆-大-丽”之后,腾冲、大理、丽江的休闲旅游正如火如荼。旺季时,双廊的住宿要靠熟人才能订到床位。同是知名的雪山,阿尔卑斯山下的瑞士达沃斯小镇既可以办世界级的论坛,也可以滑雪,而我们的西藏雪山众多,除了登珠峰,为何就不能挖掘下会议和休闲这两座金山?
临行前一天,阿旺给我推荐了两本关于西藏的书。他说:“其实很多人到西藏之前,都看了很多书,但来了往往对不上,也记不住。你既然空手来了,回去再补你感兴趣的,相信西藏带给你的收获更多。”
那夜,站在布达拉宫广场前的山头拍夜景。一堆摄影爱好者在那里抢机位,谁都想用最好的角度拍到神殿最美丽的瞬间。我踩着脚下的那一小寸土地,觉得上海好遥远,广州好偏僻……
2013.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