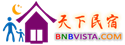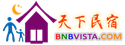聂晓光
2010年10月10日,九三学社社员、原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日语教研室主任、教授聂连增因病去世,享年92岁。
聂连增1918年4月出生,山东禹城人。1935年9月至 1942年6月间,先后在北京市私立宏达学院、国立北京大学农 学院、天津市私立东亚日语夜校学习,1942年7月至1945年7 月在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任助理、助教。工作期间,聂连增还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大学院攻读在职研究生,并在日本横滨专门学校兼职汉文讲师。(摘自高培华《河南教育年鉴》)
就是上边的这些经历,让聂连增从刚解放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近三十年时间都与“日本特务,大右派,反动技术权威,牛鬼蛇神”牵扯到了一起。这四条罪状像四条重轨深深地压在了他孩子的身上。今天,聂连增的儿子河南大学讲师,河南大学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秘书长聂晓光,在网上发表博文,回忆了自己的父亲和自己在父亲被关压年代的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原题是《我的童年时代》本文发表用了《一个右派孩子的童年记忆》
就这样我进了关押父亲的小号。进去一看里面很小,也就八九平方,父亲一人正背对着我,穿一身灰色的更生布工作服,后背上缝着一块白布,上面写着:日本特务、大右派、反动技术权威、牛鬼蛇神四行大字。看到父亲的这种情景我心里一阵酸痛,眼泪差点流出来。摘自《我的童年时代》
母亲的讲述:
听母亲说我是56年底出生在哈市南岗区满洲里街八号,那栋楼是公安厅劳改局借用哈尔滨铁路局作为办公和安置家属用的。我的出生对父亲来说是一件大喜事。一是他三十八岁得子;二是那一年他工资套改,由挣工分560分套改成货币工资,高级农艺师月薪一百五十四元,他说这是我给他带来的好事。
可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第一个不幸在我出生不到几个月时就降临啦。一次父亲不在家,母亲不太会用煤球炉,夜里炉子没有封好,我和母亲差点被煤气熏死,幸亏被邻居发现,逃此一劫。我一直感觉我的记忆力不好,认为就是这一次的事情和后来的一些不幸造成的。
记得有一种说法“人来到世间就是承受苦难的,要不刚出生的婴儿来到人世间就会哇哇大哭呢”,这个事件也就是我来到人间的第一难吧。接着就是父亲勘测规划劳改农场的工作结束,劳改局勘测大队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都被分到各个劳改农场。我的父亲因看到笔架山农场规划的最好,就去了那里。几个月后母亲也离开了哈尔滨亲戚开的那所**医院,带着我来到笔架山农场找父亲。
当时的农场条件很差,但因为父亲是高级农艺师,我和母亲来到后受到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住在场部的中心。这地方是农场的俱乐部,俱乐部的周围是被丁香树围起来的果园,非常漂亮。俱乐部的东南角和西南角上各有一座苏式风格的小别墅,我家就住在东南角这个别墅里(这里后来改为农场的电话交换台和广播站),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当时住四家。我家的对面住的是我后来的同学王玲家,那时她可能还没有出生,因为她比我小一岁。母亲说过在这里住时的一件事,有一天晚上她想出去办事,一开门看到王玲家门口有一大团綠火在烧,吓的母亲回来叫父亲。父亲拿着手电筒出去一看是王玲家门前放着一个老树根在哪里,父亲说那个树根在地下埋得时间太久啦,已经磷化所以夜里就发蓝光。第二天一问,是王玲的大哥王勇在山坡上捡来烧火用的。在哪所房子里住了不长时间父亲就被打成右派,我们家就搬到农场刚为医院建好的隔离室去啦,王玲家也搬去啦。听母亲讲,隔离室就是为有传染病的犯人建的病房,因为农场来了很多人,房子不够住,就把它改成家属用房。我们家住的在当时还算大一点的南北套间,30平米左右。父亲因右派去改造啦。房子是入冬建好的,搬进去时房子还没干透,加上东北的冬天特别冷,烧得煤又很少,房子四壁都结上了霜。这房子是用拉哈辫建的,很难干透(拉哈辫,当时一种快速建房材料和方法。就是先打上木桩,然后用草把沾上泥绕在木桩上,再在墙的两面抹上掺上草的泥,盖上草顶,墙的里面摸上石灰膏就成啦),住在哪里母亲和我遭的罪就不用说啦,早晨起来脸盆里的水都结成冰。
我的另一个同学小佳就是那时出生在这栋房子里,小佳的父亲是农场的水利工程师,我叫他的父母张大爷和张大娘,他们一家是南方人,张大娘是个大家闺秀,文质彬彬是个有文化的妇女,但是身体瘦弱多病,很怕冷,刚到东北来,冬天不敢出门,就围着被子坐在火炕上。记得张大娘喜欢吃淹臭的鸡蛋,还喜欢吃臭豆腐,并且自己会做。也许是那个年代就没有多少好吃的。小佳生下来很小,只有三斤半,大小和个猫差不多,邻居们都以为他长不大,但人的生命有时是顽强的,在哪个困难的年代里他还是长大啦。小佳比我小一岁,我们当时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在这所房子里我渡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也经历了好些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的事情。
第一件事,在我出麻疹时,母亲没注意,把我放在自留地里玩,她去除草。我在地里受了潮,得上了皮肤病。这个皮肤病除了冬天不犯,其它时间随时犯,一犯病满身长疙瘩,痒得要命,一挠就流水,然后结痂,所以我小的时候经常吃扑尔敏,弄得我上学时经常打瞌睡,甚至影响了我的学习。为了治好这个病我吃了好多种中药,记得有一种中药是用蛇皮和鸡蛋搅在一起在火上烤熟吃,这个药很好吃。这个病一直伴随我初中毕业,也就是文革中上初中期间,我和几个同学经常逃课到水库里游泳,游累啦晒太阳,晒够啦再游,就这样不知不觉皮肤病好啦。
第二件事,母亲在哈尔滨时是在我四姥姥开的妇产医院做助产士(私人企业,那时还没有公私合营),到农场后因农场是国营企业,母亲只能在农场医院里做临时助产士(那时母亲在农场接生了好多小孩),后来四姥姥的医院公私合营啦,给我母亲和农场开来了工作证明,可是母亲又患了子宫癌,不能工作啦。母亲来到农场后工作没啦,生了病,父亲又打了右派,周围没有一个亲人,好多问题一下子压在母亲身上,在精神上她接受不了,慢慢的她患上精神分裂症。那时我也就四五岁吧,记得母亲第一次犯病是在一个下午,母亲躺在炕上抽搐成一团,我吓的趴在她身上一边哭一边喊,邻居张大娘听见过来叫我赶快去找父亲,父亲回来后带着母亲到医院里看病,诊断母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那一段时间母亲每到下午就犯病,每次都把我吓的受不了。多亏当时我们农场里的几名大夫医术都很高超,其中有一个老中医姓冯,我记得很清楚,留着白白的山羊胡子,他每天给我母亲在头上扎很多针。经过一段及时的治疗,母亲得病总算好啦。
第三件事,我们那栋房子就像一个旅馆,经常有人搬走又有人搬来。在我六七岁时搬来一户姓杨的河南人,家里四男两女六个孩子。杨四、杨五是比我大一点的两个男孩,我经常去他们家里玩,可是他们一家人都患有肺结核病,有的还很严重,后来听说他们一家人因肺结核差不多都死啦。我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也患上了这种病,由于家里条件好一些,治疗及时,还算好。可是治疗那种病需要吃大量的“雷米封”注射“链霉素”,这两样药都是损害记忆神经的,在我的发育时期对我的记忆力损害很大。
在我年幼的时候正是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母亲说那时粮食不够吃,很多人都是靠野菜充饥,我家有个女邻居,她丈夫是干体力活的工人,为了她丈夫能多吃一点粮食,她每天就吃大量的野菜,有一种恢恢菜吃了后人不能晒太阳,一晒太阳人就会浮肿,这个女邻居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全身浮肿,皮肤一碰就往外流水,最后影响到心脏去世啦。那时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国家照顾,每月另外发给一些黄豆,父母经常吃些煮黄豆总算还好过些。当时农场的供销社里卖的点心都是用代食品做的,就是用一些秸秆粉碎后加入面粉里发酵后做成糕点,记得我还吃过这种食品,方方的,考得黑红有点像方形的蛋糕。
我的童年虽然遭了一些罪但没挨着饿,这得感谢史里千场长的夫人唐茵阿姨。唐茵阿姨那时是幼儿园长,六零年困难时期我在幼儿园,她利用她在农场的特殊身份到各个分场为幼儿园要来大米、白面、豆油还有牛奶。时间长啦有人提她的意见,告到政委哪里,政委就问:“她把东西拿回家了吗?她那是为了下一代,只要没把东西拿回自己家,你们就看着办吧”。由于唐阿姨的热心,当时在幼儿园的孩子们在那个困难时期都能健康成长。
史里千场长也是一个好干部,他原来是西北军军官,后参加红军,有一张与毛主席的集体合影挂在他家的墙上,解放后由于他本人文化少,屈尊来农场当场长,那时我们农场有许多向史场长这样没有文化的老革命,例如:孙(长德)大队长,老抗联,东北解放后(李保忠亲自任命的)牡丹江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不会看文件,只好降级使用在农场当个大队长。史场长把农场当成自己的家那样管理。记得母亲说过他的一件事,农场的路是砂石路,每当下雨的时候他就站在路上看着不让车过,怕把路压坏啦,看到车老板打马他就不愿意,对国家真是负责啊,那时共产党的干部向焦裕禄那样的人是很多的,他们都有着一种把新家园建设好的思想。现在想起来,我们当年在幼儿园的孩子们都要衷心的谢谢那个年代公而忘私的父辈们。
童年的记忆:
母亲生过我后就得了子宫癌,我只有一个比我大十岁的同父异母姐姐远在天津,我九岁时父亲领我回开封,路过天津时才见到她,姐姐长得很漂亮对我也很亲热,我们在一起住时她天天给我洗脚,可是由于分在两地我们很少见面。母亲的手术是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做的,那时做这类手术还很少,是比较危险的,手术后医院要求母亲每年去复查,所以我小的时候就经常跟着母亲住在哈尔滨道外北七道街的姥姥家一直到上小学。
小的时候我很淘气胆子也大,记得刚入托儿所时我和小佳在一个班,邵阿姨看着我们,晚上我们想家,我就和小佳说我有办法,我们从窗户爬出去我带你回家,就这样我们两个就跑回家啦,倒是把邵阿姨吓了一跳。
还有就是在姥姥家住的时候,由于经常在那里住,那所俄式建筑的大院里的小孩都认识我,经常在一起玩耍,就是警察抓坏蛋的游戏。有一次我是坏蛋,坏蛋要做坏事,我就拿着路边的沙子打有轨电车,打完后,小警察没抓到我,我却被开电车的师傅给抓到电车上拉走啦。其他小孩跑回去告诉我姥姥,姥姥急坏啦挪动着她那两只小脚到电车公司把我要回来。
小时在姥姥家住没少叫姥姥操心,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傍晚的时候和一个比我大四五岁小舅舅,是母亲的表弟,我们在松花江沿胜利闸那从江提上往下滑爬犁。当时天已发暗,我从江提上顺着坡往下滑,滑到下面的路上时,几辆俄式四轮大马车拉着木材赶过来,车老板没看到我滑爬犁,可是那几匹拉车的马看到我啦,在我滑到它们的面前时,几匹马叫着不往前走,一瞬间我从马的前面滑过去,车老板才看见我,骂了我一句,小舅舅站在江提上都吓傻啦。从那时我就对马有了好感,不管在哪里只要看到马都想和它们亲近一下。小的时候还喜欢去江边游泳,姥姥在院子里看不到我就扭着她那对小脚去江沿找我,大热的天每次找到我时都是满脸的汗,现在想起来真是让姥姥操心啦。
小的时候由于孤单都是和邻居的小孩一起玩耍。在那栋房子里同龄的男孩除了小佳还有铁蛋和小石头。铁蛋,他父亲原来也是公安厅老改局的干部,我父母的介绍人。铁蛋的小名起的恰到好处,长得结结实实的。小石头,父亲伪满警察,他可是名不副实,几个小孩里他最瘦小,细细的脖子顶着一个大脑袋,两条小细腿支着一个大肚子。那栋房子里还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我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好一些,父亲打右派后降两级工资但还有112元,在当时万人的农场里这个工资是为数不多的啦。所以那时我的玩具比较多,手枪、冲锋枪、木琴、望远镜、皮球、冰刀等各种小玩具,兜里还经常有些糖果。小时我比同龄的小孩长得高大一些,再加上有玩具和糖果,我在小玩伴里还是很有号召力的。经常领着小佳、石头去果园偷果,被看果园的撵得到处跑。我们这个农场当时建设的还是很不错的,农场的南半部是丘陵,山上种上了有万亩各种果树,在山里还修建了水库,(这个水库据说日本人在东北就开始修建,但没完工。)农场职工都把南半部称为花果山水帘洞,北半部是大片平原,种植小麦、玉米、水稻、大豆。场部的生活区附近也种了好多果树,所以小孩们从果树落花结果到成熟就一直在偷,不光是为了吃,也是一种游戏。再就是过年过节时父亲给我买很多鞭炮,那时的鞭炮除了现在点火的还有摔炮和拉炮。
我最喜欢的是拉炮,拉炮是炮的两头有绳,拉着两头的绳一使劲炮就响啦。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把拉炮栓到邻居的门上,再把摔炮放到门外,站到外边喊人家,只要有人出来一推门拉炮就响啦,出来撵我们踩到摔炮脚下就响啦,我家有个邻居陈阿姨,她那时没孩子,平时对我们很好,经常领着我们玩,她虽然是大人,但经常玩就不怕她,所以她就经常遭我们暗算。
想起来我淘气的事还很多。记得我们那栋房子的西边百多米还有一栋一样的房子,房子的东头住着一家姓金的朝鲜人,他是一个医术很不错的外科医生,他的女儿也是我的同学。他的家里养了几只山羊,其中有一只很大的母山羊,我经常领着小玩伴去抓山羊骑,后来我发现金家奶奶早晨从母羊肚子下挤羊奶,我看了以后就学会啦,白天就领着伙伴抓住大母羊也学着往外挤奶,没地方装就直接嘴对着喝,时间长了就被发现啦,被告到我父母那里。接下来就可想而知啦,我被父亲还被打了手板。小的时候父亲管我很严厉,家里虽然条件好,但吃饭时不管什么饭,不能多吃,也不能少吃,如果我挑肥拣瘦,就罚我不能吃饭,而且碗里不能剩饭粒。如果我淘气惩罚就是**板。我很小父亲就教我学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首诗,所以到现在我吃饭都是不多吃也不少吃,从来不剩饭粒。
记得10岁那年父亲领我回开封是农历二十九上的火车,三十晚上是在火车上吃的餐车送来的免费饺子,餐桌对面坐着一个解放军是个大校,吃饭时父亲问我吃多少饺子,我说吃十五个,吃过饭后那个解放军问我“饺子好吃不”,我说“好吃”,他说“好吃你怎么不多吃”,我说“吃饱啦就不吃啦”,然后就给他背了“锄禾日当午”那首诗,他听后把我表扬一番,“问我长大想干什么”,我说“长大想当解放军,抓坏人”。他听后非常高兴,和我父亲聊了好长时间,但我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
那次偷喝羊奶被发现后,父亲就给我买来一只母山羊,还怀着羊羔,买来后对母亲说以后让我喝羊奶(那时我每天都是买牛奶喝,五分钱一斤),羊奶比牛奶养分好,利于人体吸收。刚开始我还喝了一些羊奶,后来母羊产羊羔啦,一胎生了两个,一般情况是,把产羔后的母羊和小羊分开,把奶挤出来,一部分喂小羊,一部分留着人喝。可是小羊长大一点后,留给小羊的奶不够它们喝,饿的总是叫,母亲不忍心听着小羊的叫声,就把我的那份也都给小羊吃啦。一个冬天过去啦,小羊长大啦,三只羊吃了一车豆秸,我也没喝到多少羊奶,还是买牛奶喝,就这样又把这三只羊给卖掉啦。
——小学时最美好的时光——
上小学
1964年9月我和邻居小佳上小学啦。那天母亲和张大娘领着我们两个去学校报到,报道后在分班前还有一段时间,两位母亲就领着我们去了供销社,那是场部最繁华的地方,处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南面横在路上的是跃进门。十字路口的东南角是笔架山学校,西南角是个广场,广场的西北角有几间泥土房,是卖肉的小店和菜店,旁边还有农民的买菜搭起的木床子。西北角是一排拐弯的砖房,从西往东是被服场、食品厂(还做冰棍)、理发店、拐弯处是粮店、往北还有照相馆,修表店等。东北角就是农场的供销社。在哪里两位母亲给我们两个一人买了一个冰棍,因为那天的天气比较热,我们两个吃着冰棍又随同母亲回到学校。
回到学校一看在操场的南面高台旁正在点名分班,被叫到名字的同学分别站在三个队里,每个队是一个班。我记得一班班主任是于桂荣老师(1、2、3年级都是我的班主任)、二班是小朱老师、三班是大朱老师。我被分到了一班,记得同学有邓小林、段廷玉、李明、蒋萍、潘华、张斌,小佳好像分到了三班。
笔架山场部学校分两部分,分别在一条路的两侧,西边是小学,校长张万湖老师。东边是中学,校长是邓德进老师。小学校这边操场的北边当时空旷紧挨着变电所,操场的西边有几间草房、南边是一排红砖房,东侧是教室、西侧是小学办公室,办公室门前有一个砖沏的高台,台子南面矗立着一根高高的旗杆。红砖房的南面东半部种的是杏树、西半部种的是黄太平、大秋果。后来三四年级的时候操场的北部也盖成一栋红砖房教室。
报道后的第二天就上课啦,当然开始学的是汉语拼音,最先学的汉字好像是“人、手、足、口、耳、目,前、后、左、右。还有,屋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记忆最深的一篇课文是“五星红旗,多么美丽。我们爱你,向你敬礼。”那篇课文的上边还印着天安门和旗杆上飘扬的五星红旗。
小学一到三年级也就是六四年到六六年文革前是我最快乐的日子。那一时期自然灾害过去啦,国家还完了苏联的贷款,国内政治运动趋于平缓,父亲的右派帽子摘掉啦,成了摘帽右派,回复了工作。国家对外政治反映强烈,党中央毛主席对苏联发表了“九评”,国家主席刘少奇把精力用在了工农业建设上,经济发展很快,物资比较丰富。一年级的下学期我加入了少先队,还带上了一道杠(小队长),中队长就是班长(两道杠),小学里还有少先队大队长(三道杠)。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和同学还在农场俱乐部演出了一次节目《团结就是力量》,当时因为我长得比其他同学高大一点,在节目的最后有一个动作就是把班里最小的一个同学扛在肩上,这个同学好像就是段廷玉,那次演出也是我在学生生活中唯一的一次演出。
在那一时期我每天上学都要规规矩矩的带上红领巾,天天哼唱着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让我们荡起双桨》、《红孩子》等少年歌曲。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每天都能听到场部广播站播放的各种革命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草原晨曲》《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清粼粼的水啊,蓝莹莹的天》、《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及志愿军歌曲。那时老师给我们同学们按住处划分了很多学习小组,放学后就到同学的家里去做作业,我们那个小组里有蒋萍、潘华、李明、邓小林,做完作业同学们还能在一起玩一会,直到同学的父母下班回家。回家后我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小铃铛主持的少儿节目,那个节目的开始是一首歌“我是小铃铛,工作特别忙,小朋友……”里面还有孙敬修老师的讲故事。
那一时期父亲的心情好像也好多啦,他的工作虽然很忙经常不回家住,到各个分场去指导生产,但每逢农场举办舞会他都穿戴整齐的去参加。母亲手术后身体恢复了一些,但每年还要去哈市检查身体,可是她的精神愉快啦。那时每逢周六、日农场俱乐部都放电影,母亲是个电影迷,逢场必看,每次还都带着我,主要是怕我在家里影响父亲工作,那时父亲晚上在家时也要工作,父亲不在家时把我一个人放在家她又不放心,所以那一时期放的电影我差不多都看过。还记得有一次放的电影不让小孩看,我的邻居小马叔叔就用大衣把我裹在他的怀里,查票的叔叔只看到上面一个人头,没看到下面还多了一双小脚,我就混进去啦。
——文革开始啦——
路遇赵老师
好景不长啊,记得文革刚刚开始后的时候,母亲让我去供销社买酱油,在学校附近我碰到赵晓梁老师,他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对我很好,很远处就见到他,他在低着头走路,走到近前我举起右手给他行了一个队礼,对他说:“赵老师好!”他突然一怔,抬起头看着我,然后对我说:“晓光,以后不要叫我老师啦,我已经不是老师啦”,说完他低着头就走啦。那时我还很奇怪,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从那以后我就没再见到他。过了几天听说由于他的出身问题他被调出学校到加工厂劳动去啦。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少先队解散啦,红领巾不能带啦。随之而来的是成立了红卫兵、红小兵,我被归类到黑五类子女中不能参才加红小兵。从此我的心中被蒙上一层模糊的阴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
偶尔听到的 让我一生难忘
过了一段时间农场俱乐部那里粘了好多大字报,有一些人晚上在俱乐部附近的路上开始辩论,接着在俱乐部里有人被批判。又过了一段时间来了解放军支左工作队,队长是一位姓黄的团长,他带来一个小儿子分到我们那一班(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啦),就叫他小黄吧。忘记是什么原因他和我的关系很好,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也就是在那时,我一生中第一件对我打击最大的事情发生啦。那短时间我的母亲去哈尔滨检查身体,父亲还是经常去分场指导生产。父亲给我一些食堂饭票,我每天中午在食堂吃饭,另外每天还给我五角钱让我买一点猪里脊肉(那时的肉好像七角多钱一斤),晚上他回来就包混沌或者汆丸子。
事情发生在一天的下午,我和黄团长的儿子在场部办公室的外面玩,这时走过来一位警卫战士拿这两个暖水瓶,过来后叫我们帮他去打开水,并让我们再送到会议室去,这样的事我们过去干过好多次。我和小黄打过水后就去了会议室,走廊里没人,会议室的门开着一道缝,可能是刚才那个战士没关好门。小黄提一壶水走在前面先进去啦,这时就听会议室里面有人在说:“这次批斗会应该把聂连增也揪出来”,我听到这句话就站在了门外没有动。接着他又说:“他是我们农场的反动技术权威、右派、过去还被怀疑过特嫌,不能让他漏网”。接着会场静了一会,这时小黄出来我就把水壶递给了他,他又进去送水壶。这时会议室里又有人说话:“能不能这样,把聂连增放到下一批揪斗,因为他老婆去哈尔滨看病去啦,家里只剩一个小孩”。
接着就听那个黄团长说:“要是这样的话就放到下一批吧,反正他也跑不了”。听到这时我转身就走出农场办公室,小黄出来后叫我,我也没吱声就回家啦,从那以后再也没去找小黄玩。晚上等到父亲回来后我很想把白天听到的事告诉他,可是我没说,也不知道是什么心情,只是站在他的背后看着他做饭时心里特别难受,心里酸酸的要哭,但我又不敢哭。这件事过去几十年啦,但我一直不知道那个为我父亲说情的人是哪位叔叔,这是一位好心的人,我相信任何时候都有好心人,好心必有好报。愿这位好心的叔叔一生平安!
从那以后我的性格变啦,不在主动找同学或邻居的小孩玩,即使在同学的邀请下到同学家里也要看着同学家长的脸色。在路上看到那些革委会的领导过去认识的那些叔叔阿姨也都敬而远之,不主动和他们打招呼,这样的心情后来就变成了我对当官这的态度,一直到现在不去主动联系那些在位的领导们。
父亲终于没有逃脱被揪出来的厄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母亲回来啦,没过多久父亲就被揪出来。那时农场里有好多领导干部被揪斗出来,同时也发生了农场里最大的事情,就是被大家公认的好领导曹景堂政委因不满对他的诬陷开枪自杀。那时农场里闹得人心惶惶,很多干部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批斗。父亲被揪斗后就在没有回家,母亲的心情变得很不好。
抄家
父亲被揪斗两个星期后,我中午放学回来看到家里的房门大开着,从外面就能看到屋子里面满地都是书和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一看就明白啦,这是又被抄家啦。外面的屋地上铺着一尺多厚的书,踩着书进到里间,看到母亲坐在炕上哭,炕上地下到处是乱放的衣物,不用问这是又来抄家啦,这已是第三次抄家啦。我默默无声地开始在外面收拾父亲的各种书,分类放到箱子里。
在我收拾书的时候徐景涛大哥来到我家,他过去常来我家向我父亲学日语,见到这样的事他就帮助我一起收拾书籍。我们两个就把一些认为有用的书先整理出来,这已是我第三次收拾家里的这些书籍啦,俄文的、英文的、日文的、中文的,各种工具书、教科书、高等数学、几何、物理学、测量学、农业类的书、娱乐类的各种乐器的演奏法、五线谱、简谱、歌本、棋类、扑克类、绳子的打结和玩法、武术类的、甚至做酱油、做醋、做豆腐的都有。从中午到晚上没吃饭没上学总算把书收拾完啦。
天黑了,母亲下炕做饭,看到这些书母亲说把这些书都烧掉吧,当时我看着这些书舍不得,徐景涛大哥也不同意都烧掉,母亲:“说烧掉吧,留着也是祸害”。 我想每次抄家都得整理这些书,烧就烧一些吧,下次也能少整理一些。母亲把大 碴子放到锅里加进水,她就进到里间收拾衣物。我看着这些书感觉很难过,后来想到先烧报纸杂志吧,这些都是一期出好多,烧掉还能找到,我就开始烧报纸,一边烧一边看杂志,看到哪种杂志好看我就把这种留下来,报纸烧完后,就开始烧挑出来的杂志。就这样把一锅玉米碴子粥煮好啦。在东北做过饭的人都知道,煮玉米碴子粥是最费柴火的,而且还需要硬火,可想而知我那一次就烧掉多少书吧。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家来了一个彻底的“焚书”运动。每次做饭烧的都是书,每次烧书我都在想,烧掉吧省得下次抄家我还得收拾它。
但我偷偷的留下了两种杂志放到我的床底下,我在外屋有一张自己铺的床,一种是苏联妇女,一种是民族画报,因为我看到这两种刊物里面有很多我喜欢的东西,还有一本油印小册子不知为什么我把它留了下来,就是我在以前的博客里写得农场简史,也是那时候我留下的唯一本油印小册子,其它的油印本我都烧掉啦,还有一本一寸半厚精装本欧洲名胜古迹、人物的素描,这本书我留下来一直带到河大,后来送给一位老师的孩子,他是学美术的,这本书是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徐大哥那天临走的时候提出来带走几本学日语的书,母亲说:“你随便拿吧”。
从那次我才了解父亲过去看了多少书,才知到为什么有一些人尊敬他。但同时我也有了另一个想法,读书害己,父亲就因为看了这么多的书,才每次大小运动都跑不了他。从那以后我对学习在没有用功过。
夜半敲门声
父亲被就都出来后,过去的很多邻居和熟人在白天明面里都不敢对我母亲和我讲话啦,那时我每天去上学时都是到时间再去,课修时就到教室南面坐在墙根晒太阳,不去参加同学们的活动,晚上放学回家没事就再也不出来啦。那是入冬后一天的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和母亲都已睡觉啦,就听到有人在轻轻的敲我家的房门,我和母亲都被门声惊醒啦,母亲坐起来听了一下,房门还在轻轻地敲。母亲起来穿上衣服走到门旁边问了一生:“谁啊”,门外一个男的声音很小的说:“开门吧,有事说。”可能是母亲听出是一个很熟悉的人的声音吧,就打开了门,这时我也穿好衣服起来啦,那人很快进门就把门关了起来,棉帽子带的很低,还带着口罩。近来后就说:“革委会决定要冻结老聂在银行的存款,你明天一早就去银行把存款取出来吧,但千万别取完,留一些,以后有人问你为什么取存款,你就说去哈尔滨看病去。”那人说完话就走啦。看着母亲那很严肃的表情我也没敢问那人是谁。这又是一位我知道的好心人,在整个文革过程中这样的好心人我遇到很多。
记得母亲说过的一件事,就是我家刚去农场时带去很多箱子和两个柳条包,每个都很沉,帮助搬家的工人说:“聂技师有钱啊,这么多东西,都这么沉,”他们那里知道哪些箱子装的都是书。那时我家在银行里的存款也就是几百块钱。可是那时农场里很多的人都以为我家很有钱,因为父亲的工资在农场算是很多的啦,其实那时候父亲每月的工资一半要寄给我奶奶用于叔叔上大学和家用,另一半他还要买很多的书和抽烟,父亲那时抽烟很多还都是好烟。
第一次去看父亲
那是父亲被揪出两三月以后,革委会指派公安局的人到我家对我母亲说要让母亲给父亲送一些东西,那天下午母亲领着我去了修配厂院子里南面紧靠路边的那栋房子。那是一间很大的房子,进去后房子里面很黑,我和母亲就站在门口东面的墙边,站了一会才把里面的情况看清,里面是用木板在房子的南北搭的板铺,有十几个人在里面,有坐着的、也有躺着的,都穿着灰色的棉衣裤。看到我和母亲进来后就有人说:“老聂,杨大姐看你来啦。”这时父亲从南面靠西的铺位站起来走到母亲身边说:“你来啦”就把母亲手里的东西接过去,母亲跟着他到了他的铺位那里坐下来说话。我还是站在那里没动看着这些过去熟悉的叔叔们,他们的脸上挂着各种不同的表情,无所谓、严肃、木讷、痛苦,但都有一样的发式光头,可能是怕批斗时被揪头发吧。这些叔叔我记得的人有朱文光,刘茂任、莫百环等。这时朱文光叔叔和我说话,这些人中就他的表情是无所谓的,他和我说的什么话我已记不得啦,但他每次问我话时我回答得都很慢,因为在我还有小的心里已经知道话不能乱说、不能多说。朱叔叔和我说完话后就和我父亲说:“你儿子以后有出息啊”,父亲说:为什么?,他说:“贵人语迟,”接着又说:“等以后我们出去啦,就让你儿子给我当女婿吧”。这时莫百环叔叔说:“老朱,你还很乐观呢,我们还能出去吗?”莫叔叔是这伙人里心情最不好的一个人。朱叔叔说过那句让我当他女婿的话后,当时在场的人包括我的父母都把它当成一句玩笑,认为他是在哪里呆得没事想给大家点热闹开心。但多年后,当他们被放出的那年春节朱叔叔还真把当年在小号里的人召集到家并叫去了我的父母旧事从提,那时我初中还没毕业。
第二次去看父亲
第二次去看父亲时父亲已被移到良种站的小号关押。那时父亲的工资已被降到32元一个月,他在关押期间生活费要自理,他还抽烟。为了生活母亲又出来在农场加工厂酒坊干临时工挣钱贴补生活。母亲要上班,就让我去给父亲送东西。那次母亲让我杀了一只鸡给父亲给父亲送去(自从父亲被揪斗后像杀鸡杀鸭这类活就是我的啦,小小年纪的我已担负起家里的很多事情,像挑水、挖菜窖、堆柴火朵等)。冬天迎着西北风向良种站走真冷啊,走在路上风把棉袄都打透啦,我就只好走在路边的壕沟里,壕沟里虽然有雪不好走,可我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个我打腿绷,我冬天的时候怕雪进到裤腿里都是打着腿绷的,就这样把东西送到父亲那时都快冻僵啦。
第三次去看父亲
父亲又被转移到山南水库去关押啦,也是农场公安局的人通知的,让给我父亲送东西,并且说让我先到公安局取自行车,自行车是抄家的时候被拿走的。我过去除了小的时候和父亲去过一分场要过一个小狗,场部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那是那个冬天星期六的下午,吃过午饭拿着东西我就现到公安局找自行车,到哪里一问说是自行车前一天已被一个人骑到水库去啦,我只好沿着往南去的路向水库走去,结果我把路走错啦。去水库有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山边小路,冬天小路上没有人走,天很晴,但很冷,路上的雪很深,我那时才十二三岁,一个人走在十多里的山路上很害怕,等我找到水库的时候已是下午四点多钟啦。到那里后父亲问我:“怎么来的”,我说:“走来的”又问我“害怕不”我说:“不害怕”接着又问了母亲的情况,我都挑好的说,好让父亲放心。父亲看天已晚啦就让我回去,我说:“公安局说让吧自行车带回去”,父亲又领我在看守室找到自行车后我就往回走,开始没注意,后来我骑车时发现车胎没有气,我又不知道哪里能大气,没办法只好推着自行车往回走。这回走的是大路,但天已晚啦,一路上只看到一辆拖拉机往南走,路上再没看到其他的人,回到家里已是六点多钟,推车推的满身是汗,母亲正着急的在家等我。
第四次去看父亲
父亲又被转回良种站小号看押,这时已是春天啦。这次除了给父亲带去吃的外还有毛选四卷和两条经济烟,九分钱一盒的那种,(过去父亲抽得都是牡丹烟,差一点的也是哈尔滨烟)这烟是母亲给他买的,家里没有多余的钱只好买这种烟给父亲抽,这些东西满满的装了一提兜。我把兜子挂在车把上就去了良种站,过了幸福河的桥向西走时后面一直有车喇叭声,我回头一看是一辆解放汽车,司机还向我招手,我停下自行车,他也把车停在我旁边,对我说:“聂连增是你父亲吧”我说:“是”,他说:“你去看他吗”我回答:“是的”,他下车后手里拿着两盒经济烟问我:“是你丢的吧”我一看提兜有一条烟的包装坏啦,烟也少啦,我就说:“是我丢得”,他就把烟还给了我,然后说:“小心点,去看你爸吧,要不我拉着你吧”我说:“不用啦,我骑车就行”,接着他就把车开走啦。这位司机叔叔我只是面熟,不知道姓什么,他也是我心中的好人啊,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躲着我们这些人走的,谁还会管这些事啊。
来到良种站已是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啦,我来到看守室,看守室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我后来认识啦,他曾经是我父亲在农业中学教课时的学生。当时我要求看我父亲并要把东西送给他,他没让我进去,拿过我带去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查看,甚至把毛选四卷每一叶都反过来查看,这是我过去多次看父亲从来没经历过的。我感到很受侮辱。这时看守室又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后来我也认识啦,管德福,他也是我父亲在农业中学教课时的学生,后来我在五大队当管教时他还是我的副教导员,并在我离开农场时给过我一些教诲使我后来受益匪浅。他进来后就对前面那个人说:“你吃饭去吧,我接班”,那个人出去后他对我说:“晓光看你爸爸来啦”我说:“是”,他说:“你拿着东西跟我来,我把你锁到房间里,一会我放你出来,和你爸爸在里面多说一会吧”,就这样我进了关押父亲的小号。进去一看里面很小,也就八九平方,只有父亲一人正背对着我,穿一身灰色的更生布工作服,后背上缝着一块白布,上面写着他的四条罪状,日本特务、大右派、反动技术权威、牛鬼蛇神。
看到父亲的这种情景我心里一阵酸痛,眼泪差点流出来。父亲听到有人进来扭头一看是我马上把身子转过来,我知道他是不想让我看到后背上写的东西。我看着父亲不敢开口说话,要是一说话我就会哭出来。父亲问我什么我都是点头或是简单的回答一下,在哪里时间真是难熬啊,短短十来分钟的时间我的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管德福来啦,我看到他后就要求出去,他打开小号门把我放出来,我低着头忍着眼泪走到路上,想着回家后怎样回答母亲的问话。后来我就经常去给父亲送各种用品,看到的多啦,忍受力也变得强啦,我的性格也就慢慢的变啦。这一次看父亲所发生的事给我的印象太深啦。都是人、都是学生,在同一个环境中做事为什么会不同?
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不要欺负弱小”,从那以后我深深地理解了父亲的话。什么时候都不要瞧不起那些无权无势的弱小者,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尽力伸出你的手。什么时候都不要把那些自以为有权有势的人们放在眼里,他们自以为是,我不贪图他们的什么,我会生活得很好。有一天他们也会失掉权利,那时他们还不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