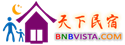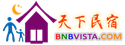2013年4月28日深夜十一点四十分,一辆由天津开来的陈旧的普通桑塔纳轿车,停在北京丰台区的京港澳高速公路入口处,在此等候的不停上了车。
车上三位来自天津的是老罗和海蓝蓝夫妇,小董。加上不停,一共四人。
二十四点整,“五一”长假期间公路免费活动开始,这辆普桑立即驶入高速,向河北方向奔去。
三十四天后,这辆疲惫而饱经磨难的普桑回到天津。

就此,一场长途自驾游结束。
这一路,是一场视觉和感觉的盛宴。
中国典型的高原,雪山,江河,森林,湖泊,沙漠,无人区,在途中尽现。那些景观和色彩,令人惊叹,甚至惊愕。
几年来,走过祖国不少地方,终有一个体会:若想看大气磅礴,气象万千的景色,只有到青藏高原。
以此推测,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昆仑山深处,该有多么令人震撼的奇景。
这一路,也是一场对胆量和体力的检验。你胜利了,你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你在经受着艰辛的同时,自然会收获着欢乐。
这一路,穿越了青藏高原上所有最高处的公路,即青藏公路、西藏阿里地区、新藏公路。
这每个名字,都令人肃然,令人敬畏。
这一路,途经天津、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甘肃、宁夏、内蒙、河北、北京、天津。
共计34天,1万5千公里。平均日行程440公里。
在此,我代表四位行者,
向西藏圣地天创演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和艺术团白团长,
向武警西藏部队某部李付参谋长,
向武警阿里地区日土县中队司机小王,
向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汽车拉力赛选手老刘,
向北京小**车主,
向一切给予我们帮助的人,表示诚恳谢意。
在青藏最高原,你们所给予的哪怕一丝帮助,都足以暖遍我们全身。
在夜幕中,车顺着高速路向西疾驶。

大家兴奋地你一言我一语,对每个人的“官职”进行了任命:
老罗开车,掌握前进方向和进程,被任命为舵手。
海蓝蓝热心公益,善于使用手机进行现场报道,被任命为战地记者。
不停眼尖,善于发现要拍摄的美景,负责瞭望。
小董勤快利索,认真细致,被任命为财务总监。
此行所开的这辆普通桑塔纳轿车,是故事的主线。
如果是开着一辆大马力的越野车,一切将会平淡无奇,不值一提了。
老罗和海蓝蓝夫妻是车主。这辆车生产于2000年,已显老态,开起来虽不时出些小毛病,但不影响走好路。而对于走新藏线,每个人心中都没底。
不停三年前乘越野车,用十一天走过阿里小环线。那时阿里已开始修路,但全线近三千公里,绝大部分仍是沙土路,颠簸不平,尘土飞扬。如果骨骼不结实,千万别去。
当时绝无人敢开普桑走阿里,烂路加高寒缺氧,那是去送死。

而现在的新藏线,就是当年阿里路的翻版。
现在阿里路早已修好,底盘低的车,只要你有胆,都可以去一试身手。
此阿里路,已非彼阿里路也。
至于青藏线,全程是柏油路,只是高寒缺氧需要意志来克服,普桑走也问题不大。
就怕问题会出在新藏线上。
对于这条线,四人都没走过,只是从攻略上看过。
严格讲,它南起西藏阿里地区的狮泉河镇,北到新疆叶城,全长1100公里。全程基本为砂石搓板路,而且坑洼不平,时有水流。中途要经过界山大阪、死人沟等极艰难的高海拔地区,还要途径广阔的无人区。
对于新藏线上冻死、高反死人的各种版本的传说,一直在驴友们中间流传。
其中一则是:一个排的解放军在执行任务中,深夜露宿在死人沟。第二天被发现,全排人员都静静地躺在地上,已经牺牲。
按死人沟的海拔高度来分析,死因只能有两条:冻死或缺氧而死。
还有不少穿越过新藏线的驴友,无论是搭车还是骑车的,所写的经历也都表述着一个词:“极艰难”。
特别是去年10月22日,一名上海白领女孩金玲,因在穿越新藏线时产生严重高反而死亡,使新藏线听来更加瘆人。

所以,穿越新藏线,成为国内外一些敢于探险的驴友跃跃欲试的壮举,也是检验一个驴友资历等级的砝码。
抱着这种敬畏之心,去年九月,不停和一脆戈、旗舰游走南疆时,专门到叶城去看新藏公路的起点。
在零公里处,已建起一座宏伟的跨公路门楼,上面立着一个高高的“0”,表示零公里起点。
对于高寒和缺氧,四人不感压力,毕竟都几次去过西藏。
老罗和海蓝蓝夫妻就曾开着这辆普桑,走过了青藏、滇藏、川藏线。现在只差新藏线了。
今天上午到达日喀则,在我们住宿的“刚坚宾馆”后院的停车场,见到一幕:除了我们的普桑,所有停泊的车辆,都是一水锃亮的越野车。它们都即将驶向新藏线,或是珠峰。
它们身材魁梧,高大结实,轮胎宽厚。我们的普桑被挤在中间,显得格外单薄。
这种差距,令人不由得会产生压力。
我们的桑塔纳从开上青藏公路时起,一路奔波,到今天准备开上新藏公路时止,已经被送到修车店修理了五次。
(穿越新藏线后,又在新疆和硕,甘肃山丹,进过修车店。)
一路上,车的排气筒被石头撞扁,颠掉、后保险杠被深坑卡掉、油泵被颠坏、轮胎被烂路扎漏、怠速偏高、打不着火。。。。。
至于我们自己在途中修车和下来推车的节目,每天都在上演。有几次是自己推车不见成效,只好请其他车辆挂上绳索把车拖着火,再继续前行。
昨天上午到达拉萨后,在布达拉宫附近的“西藏天域交通宾馆”的贵宾楼住下。
下午三人去八角街。不停无意逛街,休息片刻,在宾馆给白总打电话。
白总是著名的西藏圣地天创演艺公司副总经理和艺术团团长,内蒙人,身体健壮,热情坦直,豪爽善饮,颇有蒙古族汉子的范儿。
他在拉萨工作多年,可以说是一位老西藏。

三年前,不停和白总的同学到拉萨旅游,就受到他的热情接待。
圣地天创演艺公司的大型西藏歌舞音画史诗《喜马拉雅》,气势宏伟,演技精湛,是一场了解、触摸西藏和藏文化的视听盛宴,极有价值。
而节目演出的剧场,是世界首创的富氧剧场。也就是说,剧场在演出时供放氧气,使观众感到舒适。
通话后,白总立即请我们到剧场来看演出。
四人非常高兴。
晚八点节目开始。
白总把我们安排在中间的位置。
观看这场演出,给我们这次的青藏高原之行,增加了绚丽的亮点和色彩。
一场藏民族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啊。。。。。,面对昆仑,连着冈底斯,念青唐古拉,
唵嘛尼叭咪吽喜马拉雅,
阳光多么灿烂
温暖像慈祥的妈妈
雪域多么富饶
江河在这里发源
啊。。。。。喜马拉雅
辽阔的高原
美丽的家乡。。。。。。”
这首主题歌,顿时使观众感到,自己已置身在蓝天白云,雪山皑皑的青藏高原上。
演出结束,白总对我们去南迦巴瓦峰和其他景区,提出了具体建议。
在青藏高原,有这样一位朋友,是一种真诚的情缘。
这场演出,无形中振奋了四人的精神,西藏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力。
无论新藏线有什么样的艰辛,明天,我们都将上路。
今天从日土县城正式踏上新藏线。
原准备早六点出发,争取在一天内穿过海拔最高的地段,但天色一片漆黑。躺到七点,吃了一个自备的馒头,冲了一碗奶茶喝,天色已亮,开车出发。
一开始还是柏油公路。走了约十公里,开始全线修路,老路被土堆堵住,却见不到一个工地人员。车辆全部下到路基下的旷野中,在无边的沙滩中自寻出路。

我们的普桑沿着大货车压出的沙坑路,颠簸摇摆着前行。
浓重的尘土从车厢的各条缝隙中窜进来,车厢里乌烟瘴气。
海蓝蓝及时向朋友们发出一条微信:坐在副驾座上打盹的不停被尘土呛醒,眼前黄尘一片,看不见东西。他问:“是老罗在开车吗?”
左侧的尘埃中传来老罗剧烈地咳嗽声,他喘着气说:“就是我在开车。 ”
这条微信,后来被大家定为一路上所发的最佳微信。
尘土还可以忍受,路况却极差。跌跌撞撞行驶了三十公里,在班公湖东侧爬一个大土坡时,车的右前胎被尖石扎漏,车停下来。
老罗取出备胎,不停把扳子套在被扎坏的轮胎的螺丝上,用脚使劲向下踹。螺丝很紧,踹了两下没松动,不停跳起来踹,一口气卸下来四个螺丝。
又把新轮胎安上,使劲用扳子把螺丝拧紧。
海蓝蓝在一边提醒:轻点用劲,小心高反。这里的海拔是4300米。
轮胎换好了,但车再也打不着火。
老罗挂上倒档,把握方向盘,其余三人向下推,车歪歪扭扭向下溜了十多米,依然打不着。
高原的烈日像火盆一样炙烤着浑身是土的四人。不停的手无意间碰到了上衣的金属拉链,竟然像被烙铁烫了一下。

折腾近一小时,大家已气喘嘘嘘,只好求助过路车。
在一小时之内,拦住了三辆从新疆来的大货车,但大车司机都不懂小车,帮不上忙。于是拦住第四辆大货车,请司机把普桑拖到坡下的公路上。
四人无助地坐在地上,盼望能有轿车经过。这也许是奢望,因为新藏线无法走小车。
等了半小时,远远地,沿着湖边真的驶来一辆轿车,拖起滚滚黄尘。
驶近了一看,竟然是普桑!
车被我们拦住,司机和一位老者下来,把我们的普桑检查了一遍,告知说,是油泵出了问题。
原来他们是到前面不远处看公路的施工情况,而后返回日土县城,根本不走新藏线全程。
如果要修油泵,只能回县城。但如何把车拖回去?
大家想到一个办法:拦车。由不停坐被拦住的车回县城,请一位修车师傅开车或打车,带着新油泵来换件。
这一往返六十公里,路况恶劣,修车铺敢宰你五千元。在这种人烟罕至的地方,他们能宰一个是一个。
上次有个朋友在高原上换了车上的四个螺丝,竟然被宰了四百元。
但有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不是油泵坏了。如果判断错误,带来换件也没用。
大家又无语了。

究竟怎么办,一时成了比烈日爆烤还煎熬人的问题。四人默默地各自找阴凉地坐下,一筹莫展。
此刻,有三辆武警标记的越野车从日土方向沿班公湖驶来。
凭着当过兵的感觉,我们觉得有救了。
车驶近后被我们拦下,三辆车的武警全下来了。
根据军衔,我们看出其中的首长,便把困难向他说了,并说明我们都是曾经的军人。
三位小车司机检查了普桑,也认为是油路的问题,必须要到日土县城去修理。
那位首长当即用手机给日土武警部队的领导打电话,让派车来把普桑拖回县城。
这一切,解决的如同炸掉一个敌碉堡般利落,我们十分感激。
目送武警车辆远去后,四人再次坐下等待。
老罗已忙碌半天,一身尘土,现在索性顺大坡下到班公湖边,坐下来看鱼和野鸭。
第一天住的那家宾馆已没有空房,我们在附近的招待所住下。整个日土县城,仅有三家宾馆和招待所。二十分钟可以走完全部街道。

招待所里没有厕所,上厕所要到外面一百米的地方。老板在走廊上摆了几个铁桶,住客可以对着桶解决问题。
出师未捷,车被拖回。这个失败给大家带来焦虑:我们的普桑究竟能否穿越新藏线?
经商定,大家一致决定:无论有多大的困难,继续走!
两位女士,海蓝蓝和小董,表现出了格外的坚定和勇敢。
早七点起来,每人吃了几个剩饺子,喝足了水,装车,准备再次出发。
不停昨晚睡觉时感到头疼。这是昨天过于用力所致。白天活动过度后,高反一般就在晚上出现。
车修好了,今天是能否穿越新藏线的关键一天。
或是胜利穿越,实现夙愿;
或是中途再次抛锚,甚至是深夜,抛锚在高寒缺氧的无人区,后果难料;
或是半路后撤,终止穿越。
重要的不是你开车穿越了新藏线,而是你开着什么车穿越了新藏线。是普通车还是越野车,是车队还是孤车。
越野车队很少出现问题。即使出了问题,也有同行者相助,哪怕是在无人区。所以,穿越者的心理压力不大。

我们不同,开的是一辆陈旧的、多次修理的普桑孤车。
明知前路有危险,却执意前行,这就带有一种探险或冒险的味道。
我们似乎更接近于后者,因为我们的装备差。
四人再次研究了已看过的攻略。由于这些攻略含糊粗放,我们自己作了计算。
新藏线从日土县城到红柳滩,共450公里。
其中从红土达坂到奇台达坂共208公里,除了在甜水海有一小段是海拔4857米,其余全在海拔5000米以上。
依据昨天经历过的恶劣路况,假设车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行驶,仅这最高海拔的208公里,就要走八个多小时,而且全部是在深夜。
这一路寒冷缺氧,一旦车抛锚,可能只剩下在严寒和缺氧中等死。
假设在中途住下,第二天白天继续前行。即使抛锚,也比在深夜安全系数大的多。
但途中只有多玛、死人沟和红柳滩可以住人。

死人沟历来名声恐怖,在驴友中流传着许多传说,听听这名字,就足以令人战栗,决不做住宿考虑。
而多玛和红柳滩两处相距342公里。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行驶,要走近14个小时。
到多玛住下,天还不黑,有些浪费时间。
而到红柳滩住下,那就是后半夜。之前要走很长的夜路,抛锚了怎么办?
四人最终的意见是:路况不明,先走着看。
其实有一句潜台词在刺激着我们:冒一次险,走新藏线海拔最高的夜路!
八点十分出发,沿着昨天走过的路,再次来到普桑曾抛锚的土坡前。
昨天武警司机小王说,土坡左侧有一个隧道可以走,出隧道走一段土路后,有一条小路拐向山坡下面,通向刚铺好的柏油路。
于是我们的车没有爬土坡,穿过旁边的隧道,沿着一条土路走了一段,却开始爬坡,进了荒山之中。
被大货车压烂的土路坑洼不平,越爬越高,蜿蜒在荒凉的群山中。

这漫长的山路,使我们想起了昨天抛锚的土坡,不禁有些紧张。
此时小董说:小王说出隧洞后,有一条土路拐到柏油路上,它应该在离隧洞不远的地方。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老罗把车掉头,驶回去找那条隐秘的土路,果然找到。
沿着它行驶了一段,拐上了新修好的柏油路。
大家说应当奖励小董。研究半天,想到的奖励方法是:下次吃饭时坐在上席。
并将它定为一条四人间互相奖励的规则。
正当大家飞奔在柏油路上,幻想着一路轻松到达叶城时,走了仅十多公里,路面被土堆堵住,只好再次拐到下面的荒滩上自谋出路。
普桑底盘低,只能压着荒滩上过往的大货车的轮子印走。
但路中间经常出现沙坑,普桑过不去,便退回原路另寻出路。
于是,老罗在车上等待,其余三人下车探路,分头沿着几条大货车轮印步行,瞭望前方是否平坦。
在高原的烈日下,三个人行走在荒漠中,像三个黑点。一旦谁发现了可走的路,就向其他人高喊。
但这声音立即被高原的烈烈大风刮走。最后只好用挥手来表示。
确定一条路后,在后面等待的老罗把车开上来,三人再走过来上车。
有时有刚筑起的砂石路基,车可以开上去。但路上横有二十多公分高的突起的水泥梁,普桑底盘低过不去,要三人下来,车小心地越过横梁,三人再上车。
每两根横梁间的距离约几百米,车要不断减速上下横梁,三人要不断上下车。
这些动作耗费体力,三人感到胸闷气喘。
大家很快总结出,此刻什么是幸福。

太阳不这样酷热,风沙小些,就是最大的幸福。
不推车,不下车,不探路,就是最大的幸福。
能见到人和牲口,就是最大的幸福。
路上有河水流过。一辆大货车装载过满,前轮陷在河水里,动弹不得。司机正站在车下发愁。
三人下车找狭窄处,蹦跳着过了河。老罗小心地把车开过河。
那位司机如同见到救星,对不停说,前方路边有一个公路施工项目部,请转告他们,大货车陷到河里,让他们来救援。
问他项目部离这里有多少公里,他一脸茫然,说不上。
在这片无边的高原上,极少有里程碑。加上所走的路脱离了原来的公路,已分不出距离的远近。
高原上没有信号,无法和对方联系,只能托过路的车辆捎口信。
对于这种请托,受托的司机是必须要办到的。在人迹罕至的高原,这是为人的原则,也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不停请他放心,一定把话捎到。
普桑继续前行。不停一直在考虑:现在离界山达坂还有多远?几点钟能过?
如果在太阳落山前还没到界山大阪,太阳一落山,气温将降到零下,风势会更大,行路会更难。
即使马上到界山大阪,还要走一百二十公里才能到死人沟。再赶到红柳滩住宿,就该是凌晨了。
所以,尽快赶到界山大阪,从心理上和路途上,就像过了一道关口。
走了一百多公里,只见到两个修公路的住人点和一个骑摩托的藏民。问他们界山大阪还有多远,谁也说不清。
这一路碰到的人,对里程的概念都很含糊,说不出从哪里到哪里的距离,这是否是一种高原特色?
走了两小时后,路边出现一座临建小院,这就是项目部了。
不停下车时,海蓝蓝说:带上暖壶,向他们要一壶开水。
这是个好建议。假使车抛锚,在这荒原的寒夜里,喝口热水也可以暖暖身体,
不停拎着暖壶走下路基,向两百米远的项目部走去。就是这样一段距离,走起来却感到气短腿软。
不停走进小院,见到房屋都是钢架结构的简易建筑,但很结实,里面很暖和。
一间屋里有一位中年男子,一位女孩,都是藏族。不停把口信传达给他们,要了一壶开水,拎着向回走。
两百米的路,走得胸闷气短。坐进车里,半天缓不过劲来。
不停顿有所悟:也许项目部可以借宿。
再向前走,就是新藏线的最高处界山大阪了。
四人今天已经在高原上奔波了近十二个小时,车疲人乏。
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在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时候,当普桑拐过一个小山坡,路边一块两米高的黑色大理石石碑,猛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上面写着硕大的红字:“界山达坂 海拔5248米 武警交通八支队”。
四人大吃一惊,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里就是界山大阪?
这里就是那个新藏线的名片和标志,那个说起来令人色变的地名,那个令无数驴友敬畏的地方?
我们手忙脚乱地下车,走到石碑前,在大风中一字字大声地把上面的文字念了一遍,终于确信,这里就是界山大阪。
大家看了时间,晚上八点五十五分。在内地,此刻已是华灯万盏。
但在这里,红日正悬在西山顶上,金黄的余晖照在从石碑上方,斜射在四人的脸上。
我们在那一刻,胸中升起一种成就感。
所幸的是,进入新疆境内后,路况有所改善。尽管是时而搓板,时而柏油的黑白混合路,但比起前面走过的荒滩野路要强得多,车速达到了每小时30公里。
这样,120公里的死人沟到达是在深夜一点左右。
太阳已经落山,四人在暗夜中前行。
新藏线的夜晚,诡谲,神秘,寒冷,缺氧,充满不详。
路上极少有车。过往车辆绝大多数,已在有限的那两个能住的地方住下来。
还有的大货车停在海拔低的路边,经验丰富的司机们,在后座上铺开所带的厚实被褥,准备过夜。
只有我们的普桑,亮着两盏刺破黑幕的大灯,疲惫而倔强地行驶在世界之巅漫长的搓板路上。。。。。。
许多资深驴友说过,去西藏会“中毒”。

感谢他们,创造了这样形象的比喻。
去西藏确实会“中毒上瘾”。仅说我们四人进藏,不停五次,海蓝蓝四次,老罗三次,小董二次。以后可能还会去。
原因归于这次走新藏线,更强地引诱出我们的瘾头。
去西藏,不光是去看景,更多的,是去寻找不平凡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