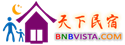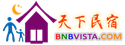风是黑夜,雪是清晨。
是夜,4800米的高山,三个男人挤在帐篷里,测着心跳测着血
氧,吃泡面泡饼,喝80度沸腾的开水,听自己的音乐听同伴的鼻鼾听
帐外的风声。风,时急时缓,急时,如神推鬼拽撕扯得摇摇欲坠,揪
着的却是焦急的内心,明晨若狂风不止,是否安全?可否攀登?缓
时,如情人私语般轻抚着,夜静星空,老聂突然一句“人品好就有好天
气”,心静了,自然入眠。待得听到哈巴的叫声时,已然起床时分。
5396接纳了我们,给了三个小时的开窗时间,一路向上,雾浓雪深
,却极静,没有风声.。心跳和呼吸之外,就是同伴同样喘息着的鼓
励,顶峰的木桩被雪掩盖得只有矮矮的一段尚在,有红色的围巾或是
经幡缠绕,冰雪已经将它们和木桩结为一体。
刚下撤,前行不过十数米,雪至,风仍不大,卷起的雪粒吹打在
脸上却依然烈烈生痛,雾气更浓了,同伴的身影在数米外就几不可
见。向下看,雪坡没有尽头没有终点,回望,只一条深蓝的路绳在满
天雪雾中升向天际,同样的,无始无终。一步步,不知觉间,雪已过
膝,不时的需要坐下,将那深埋进雪里的腿拔出,再拔出,扣锁开
锁,过结点再过结点,雪沾在眼镜上紧紧相贴,久久的不愿融去。缓
缓走来,心却也不再有上攀时的焦急和期盼,帐篷就在那里,一如“山
就在那里”一般。上和下,进和退,回忆与向往,追寻与放弃,在飘雪
浓雾的山间,竟浑然一体。走过一路,终得见,那柔柔的橘红间,撒
满了银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