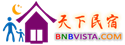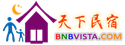七月的时候在巴黎,走了一夜的夜路,睡下已是凌晨四点。
第二天的一大早,朋友已经离开去了凡尔赛宫。十点接到泡面的电话,叫醒我记得去楼下吃早餐。
大概是头一夜太过疲惫,精神还没有恢复。下楼在餐厅里,一边夹起一块餐盘里的羊角面包,一边喃喃开始跟身边的J同学说起话来。自顾自地言语了半晌,发现对方没有回应。回头一瞅,那穿着湖蓝色套头衫的高个年轻法国男人正看着我回报以微笑。原来是认错了人。
连忙道歉解释,他倒是很友好,一只大手拍在我臂膀上说“Don‘t worry.it‘s ok".
端着选好的早餐,走到一边的桌子坐下,开始默默计划这一天。奥赛博物馆是想去的,当然还想再去一次细细看看蒙马特高地,可拉雪茨呢?
拉雪茨。这个名字是刚刚进入巴黎的第一天就看到的。住的旅店在离那儿很近,来的路上,车子经过,周围似乎很安静,是一条条纵横交汇,时而又上坡的小路。
记得那天车子行至一半,在拉雪茨附近停在路上等待前面一个房门口一辆大车倒车的时候,抬头看见路边公寓的三楼窗子边有两个年轻的法国男人,他们挥手向车子玻璃里的我们问好。那微笑温暖地像一道阳光照进他们窗子的景象一般,像在电影里一样,暧昧又带着些异域浪漫的味道。
那块地方于是从一开始就带给我无限的幻想。我想,就去那里吧。
早餐过后,简单收拾了东西,拿着旅行地图出门。沿着地图,按图索骥,那似乎确实只是半小时以内,就可以走到的距离。
一路上人很少。街边的有些制衣的店铺,好些是亚洲人开的,他们长着亚洲人的脸孔,却以流利地法语交谈。还有些看上去似乎很久没人光顾的五金铺、印度人的便利店、小餐厅和经过一夜欢愉后疲惫的酒馆。
这里并不难找到,穿行在小巷之间,约莫走了二十分钟,就来到了。
一个石阶沿墙向上,转身后是一个小侧门。看了看地图,没错,是这里了。可是,他怎么会只有这么小的门呢?难道是因为墓园的缘故?我百思不得其解。而直到整个漫游的结束才了解,那天那扇石阶通往的小门其实只是个边门罢了。

(拉雪茨神父公墓的正门)
拉雪茨自然是埋葬着很多名人的。各种不同的宗教也在此相安共眠。
这不光是一个缅怀的地方,墓园中几乎处处都是可以值得观赏和沉思的地方。树荫遮蔽的小径,小教堂前树荫下的长椅,长椅上坐下,可以远眺俯瞰到巴黎。
身边的长椅上,人来了又走。一个看似是中国人的姑娘,独自坐下,我们默契地没有说话。通常在异乡,两个单独的旅人是会寒暄几句,或者相视一笑。但那天一切都安静极了,谁也不想有任何的举动破坏这宁静的氛围,好像任何的攀谈都是一种对它的亵渎。所以我们选择了留给彼此距离,得以给自己的思绪一些漫溢的空间。
我有时候在想,那些独自坐在长椅上休息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在想着什么。是和我一样的游客,还是来祭奠自己长眠于此的亲人或者挚友,或者天人相隔的恋人?
我坐在那里,看着树冠后隐隐若现的巴黎,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我真的是在这里吗?就在此刻,周围安放着无数的魂灵,那些名字对许多的人,对从前的我,是多熟悉又多遥远。


一个人闲步在墓园中,辗转多次,花很久时间看懂地图上曲折的小路。去了浪漫派的画家德拉克罗瓦前瞻仰他。这条墓园小径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熟悉的名字。
接着是阿波利奈尔。他和他的夫人葬在一起,墓碑上刻着两人的名字。他死的时候,她才二十七岁。
粗面的花岗岩墓碑上有盆盆鲜红和黄色的花,下面印刻着一首诗,诗是心的形状。
这他留给爱人的诗:”我这颗心像是一株倒过来的火苗”。这位超现实主义的开创者,在晚年写诗喜欢状物,颇有些意象主义诗人的风格。


从他的墓离开,不知不觉来到了中央墓园。
这里的墓没有碑,只是简单的安放着逝去的人的照片。像一块块彩色的磁贴,在墙上一字排开。Maria Callas就在这里长眠。
偶尔有人漫步进来,一边走,一边扫视着墙壁上陌生的名字。有时驻足片刻。
听说卡拉斯的墓很不起眼,她的骨灰撒在她最爱的爱琴海。这里没有她的相片,但总有来看她的人送上一束鲜花。很多人会亲吻她的墓,留下只字片语,甚至痛极时悲泣。
这样一个柔美的花腔,曾经带给数代人多少的感动,无从考究,也无法想象。他们相隔着时空的距离,素未谋面,却因为她的声音,两个陌生的灵魂得以穿越时空共鸣。



89号墓并不难找,那几乎是整个拉雪茨里最热闹的地方,从来不缺到访的人。
你一定不会陌生,王尔德就在这里。

“Paris, Je T‘aime”里,那个固执的去亲吻他墓碑的女人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我一直好奇,他是有怎样的魔力,要让世上的女人都为他疯狂?
从到,,人性的欲望、情欲和死亡,无一不深深触动着我。可这个去世后被女人追捧的男人,却是写下"a love that cannot speak its name",在当时无法被社会接受的同性恋。
他的墓碑是一个死后,一个迷醉于他作品的女人出钱修建的。墓碑上周围的玻璃上密布着红色的唇印,和来自世界各地,持着不同语言的景仰者留下的字句:“谢谢你,王尔德。谢谢你的存在”。
他是行走在世界的千万人里,黑暗中抬头仰望星空的那一个。密布在墓碑上亲吻的唇印让他成了这个严肃的园林里浓艳的一笔,仿佛他的存在,是那个保守时代里讽刺的一记。
就要转身离开,瞥见在石碑底座上刻写的一句话,读来-- “Here Lies the Best Man Who Ever Lived."



墓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概除了像王尔德、肖邦、罗登巴赫这一类的名人,就是那些被死亡、忏悔意象笼罩的雕塑和墓碑上的字句了。甚至有时候,他们的存在会带来更意想不到的触动。
比利时的哲学教授Fernand Arbelot捧着妻子的脸对话的雕塑,穿着长袍挡着脸,从监狱小窗伸出手,和牢狱里丈夫紧握在一起的女人阴暗背影,悲伤的母亲和襁褓中已经离开人世的婴孩。
一生被死亡意念缠绕,写的比利时诗人Rodenbach,与死亡缠斗的他手持玫瑰,正企图从坟墓中爬出的样子。
许多墓上,有来访的人留下的烛台,印刻着字句的相框,写着对朋友或亲人的思念。记得远远看见一个祭拜的小墓室里,一个战战兢兢的老人正拿着扫帚和布,仔细清理着。有些墓却已经破败不堪,杂草丛生,仿佛很多年没有人再来看过了。我很怕看到那些已经破碎或者破旧不堪的烛台、法文写着"A mon amie pour toujours"已经在风吹雨淋的中腐蚀的纪念牌,或者甚至是石碑已经裂开、名字也无法再得以辨认的荒墓。他们被孤独地埋在此地有多久了,会不会冷?后来的人是不是早已经忘记在这个孤独的世界上,还有他们的存在?
在墓园里一切都变得很真实,这是接近死亡真相的地方。不论墓穴好坏,修缮的是否高档,雕刻是否精美逼真,睡在里面的灵魂都是一样的。墓穴里的人已经去了,带着对人世的忏悔、留恋或者解脱与平静。墓穴外的人,靠着镌刻的字句、火烛和鲜花缅怀死者,也在十架和墓穴前审视着自我。我们从尘土来,又归于尘土,如果不曾留下什么,这一遭走的又是为了什么?

(这墓碑上的是一对夫妻,犹太教的标识下写着的是"永不再分离”。)

沿着墓园中央的石阶走下,漫不经心翻看着拉雪茨的介绍,突然一个名字映入眼帘,Heloise et Abelard.怎么会?
印象中,他们一直是存在于文学中的人。故事是真的存在的,可是因为对于那Alexander Pope的诗过于熟悉,总让我觉得这样的两个人是虚构的,是只存在于诗人创造的音步韵脚之间。
1114年,36岁才华横溢的修士阿贝拉尔成了17岁的艾洛伊斯的家庭教师,她精通拉丁文和希腊语,是叔父小心翼翼培养起来的巴黎才女。相处的越长久,感情便与日俱增,他们无可救药的爱上对方。但这爱情不能得到祝福和认可,在那个基督主导的时代,这是大逆不道的。他被她的叔父赶走,并勒令两人永不能再见,而这阻止却让艾洛伊斯和他的爱情更加炙热强烈。她偷偷地同他见面,最终怀孕,生下了他的孩子。为了阿贝拉尔作为修士的声誉和前途,艾洛伊斯秘密地与他缔结秦晋之好,却也刻意将此隐瞒于世。
她的叔父知道了此事,认为他欺骗了纯真的艾洛伊斯,盛怒之下,他派人冲进他的房间,阉割了他。从此,他们双双进入了修道院,到死也再未相见。
此后的很多年,他们一直通信,写下的书信被后人编成了书信集,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人间的悲剧被蒲柏写成了同名的长诗。原诗很长,读来是形式和字句都很美的,其中一句被金凯瑞的电影引用,我想同你一起分享。
"纯洁无暇的人是多么的幸福,
遗忘世界的人,世界也把他遗忘,
无暇心灵中的阳光永恒灿烂,
每一个祈求都被接受,每一个愿望都得以实现。”
How happy is the blameless vestal‘s lot!
The world forgetting, by the world forgot.
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Each pray‘r accepted, and each wish resign‘d;
这是艾洛伊斯的书信中绝望的爱恋,修道院已是她最后可以得庇护的地方,即使是在那里,只要听到阿贝拉尔的名字,他的呼唤,她便无法再能抑制自己的情感,保持平静的祷告,心中的那团爱火又被点燃,接着任由火焰将自己吞噬。苦难没有终结他们的爱,这绵长的爱恋一直持续到两个生命的终结。
这对尘世间的至爱在身后永远结合在一起。1142年阿贝拉尔在圣马塞尔修道院去世,后来遗体归还圣灵修道院。1163或1164年,艾洛伊斯去世,被埋葬在阿贝拉尔身边。他们的遗骸后来多次迁移,19世纪最终迁至巴黎,直至今日。
我走来园子的东南角,一片坟冢之间,他们的墓很容易被认出。阿贝拉尔和艾洛伊斯被安放在一个亭子里,石棺上的他们双手合十,安静地躺在那里,日日夜夜向上帝祈祷着。墓的四壁刻画着他们故事的浮雕,和法文书写的记录。这对中世纪的爱侣,几百年后,终于可以相聚在一起。
去年的冬天,又重温了金凯瑞的电影和这首诗,一句一句细细读来,爱不释手。没想到,会在夏天的拉雪茨意外地相遇这个故事里的他们。

这世上,有多少爱情倒在现实面前?几百年后,又有谁会每年如一日地像阿贝拉尔和艾洛伊斯靠书信作为在孤独世界中唯一的慰藉,相互支撑着彼此直到生命结束?
那天墓园里,阳光星星点点从这片墓区树林的叶子缝隙间泻在蜿蜒的小径上。很少有人经过,也没有人在他们的墓前停留驻足。与其他的那些墓前访客不绝的艺术家相比,他们好像格外孤单。大概生前经历爱恋的轰轰烈烈也早已让他们疲惫了吧,这死后的宁静是多么不易。
在围着他们墓碑的石栏外,我单单站了很久。中世纪的浮雕里的小人,浮雕表面脱落以后斑驳的石壁,好像带我回到了那个黑暗,绝望的时代。我好像看见,艾洛伊斯的呼喊,像她法文名字的意思一样,变成一颗颗暗夜中的星星,照亮着阿贝拉尔寻找她的路。
离开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刚刚站立过的地方又空空的了,他们仍然熟睡着,表情安详。九百年前的悲剧已经平息,故事里的人、那些阻碍的力量都已经不在,也被淡忘了。但他们的故事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向活着的人传递着力量。
知道他们故事的人也许并不那么多,甚至可能会越来越少,而会去耐心读完蒲柏晦涩长诗的人则更少了。但至少那个冬天的早晨,它让我感动到落泪了。至少在巴黎的这次不期而遇,让我对拉雪茨漫步的一天再不能相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