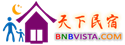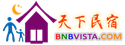题注:以为14天的假期可以走完整段川藏北线,做了功课才知道几乎不可能,或许紧赶慢赶能赶到,但那不是我要的旅行。所以干脆把川藏线一拆二,这次只走西藏段,把四川段留给下一个假期,所以就有了“川藏线(上)”这一说。
春节去黄南果洛的时候就想说说旅途中遇到的那些人,回来后一犯懒就搁笔了。记录旅途中的“那些人”并非为了褒贬什么,只因为他们的真挚和有趣一直以来深深地打动着我。
这次出发前曾无情的拒绝了几位朋友同行的要求,心里很是歉疚。不过我知道在关闭朋友这扇窗户的同时,已经打开了同陌生人的遭遇和交往――这扇同样有趣的窗户。
青年旅舍
青年旅舍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有点像武侠小说里,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也许就是个绝世高手。特别在青年旅舍的多人间混过以后,你肯定会同意我的说法。
我是坐飞机到拉萨的,副作用是当晚就有点高反――嗜睡不已,晚上九点不到就躺在多人间的上铺迷糊了。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在介绍川藏南线的资讯,说的非常详细,从班车时间、票价,到每一站旅馆名字、方位,再到一路上有名的、没名的景点。一开始我以为有人在读哪本攻略书,挣扎着睁开眼一看,却是一个男的在随口说着,不禁有点不服气的拿出我准备好的攻略对照一看,居然八九不离十的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大家叫他蓝老师的家伙已经第七次进藏,对于藏区的攻略早就烂熟于心、倒背如流。
蓝老师川藏线的资讯是说给我对面上铺的哈尔滨女孩听的,虽然蓝老师说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可是哈尔滨女孩还是一脸茫然。蓝老师不禁有点泄气:“你来拉萨都快两个月了,怎么对你下一步行程还没有半点概念?”
“我挺喜欢拉萨的,想找份工作生活下去。”哈尔滨女孩幽幽的说:“这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才想出去散散心嘛。”
这个哈尔滨女孩大概是我见过最赢弱的东北姑娘了,个子不高、身体单薄,还带着副斯斯文文的眼镜。我的好奇心被勾起了:“那你这两个月都在拉萨晃,没去别的地方?”
“去过纳木错。”她推了下眼镜,仿佛才发现对面上铺还有个人。
“包车去的?现在多少钱一辆车?”我继续着自己的好奇。
“我是和别人骑车去的”她说的若无其事。
我怀疑自己听岔了:“骑自行车?不会吧?那得骑多久啊?”
“骑了两天半才到,屁股疼死了,从来没骑过那么远。”她说的仿佛从人民广场骑到佘山一样。我却知道从拉萨到纳木错一路上坡,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一路上至少要翻越两个5000多米的垭口,我在这么高的地方不要说骑车,连走路都气喘吁吁。至于骑车,我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我想象着她在高海拔骑车呼吸的艰辛,不禁自己呼吸急促起来,蓝老师和哈尔滨女孩好奇看着我,以为我身体哪儿不舒服。
我回过了神,不好意思的冲他们笑笑,刚想解释怎么回事,一个穿着红色冲锋衣的女孩子像一团火一样冲了进来。一进来就大喊:“太好了,太好了,终于又回到了拉萨!”
“你们知道吗?”她兴奋的说道:“我下了火车直接就去看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连行李都没放下。”不等有人搭腔,她连珠炮似的说道:“上次来的时间太短了,根本看不仔细,这次好了,辞了职,可以一个一个慢慢地看了。”
大家有点不知所措,没有人搭腔。不过那个女孩子一点都不介意,自顾自地继续说道:“上次有钱没时间,这次有时间又没钱了,真矛盾啊。所以这次只好买硬座票过来了,售票窗口还好心提醒我还有卧铺票,我只好跟他说我穷没钱。唉,没办法。”
尽管没人搭腔,那女孩却突然愁眉不展起来:“我坐了55个小时火车几乎没怎么睡过,到了这里又去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可是我现在还是很兴奋,一点都不困,估计今天晚上又要失眠了,你们说该怎么办呀?”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那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之后我就昏睡过去了,不是因为高反,是因为被震撼了,并且不想继续被震撼下去。
班车和班车司机
从拉萨到八一的班车有很多种,我坐的是十一座的金杯,车上除了我包括司机都是藏族人。我坐在中间一排靠门的位置。坐在我后面是个藏族小伙,个子不高,瘦瘦的,上身的西装袖口上缝着商标,下身穿着一条很旧的牛仔裤,他在车上只做两件事,抽烟和吐痰。有时候抽完一口烟吐一口痰,有时候吐完一口痰又猛吸一口烟。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年轻的藏族妇女,她也只做两件事,睡觉和呕吐。她早饭一定没吃多少,因为吐了10分钟后就开始干呕了。接下来7小时干呕声一直断断续续的伴随着我。而坐在我左边的是个威猛的藏族大汉,他比较纯碎,只做一件事,打电话!从车还没出拉萨开始打,一个接一个的打,并且用超过80分贝的音量大声的说、大声的笑。第一个小时我尽力忍着;第二个小时我开始奇怪一个人怎么能连续说那么多话;第三个小时我开始佩服这位大汉能连续大声说三个小时而不口渴;第四个小时开始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再听他说下去,我的左耳很可能会失聪的;第五个小时,幸好没有第五个小时了,我们终于停车吃饭了。下车后我的左耳果然嗡嗡作响,于是重新上车后我要求和大汉换个座位,我不喜欢单边作响,两边一起立体声嗡嗡地响会舒服一些。没想到车才开出半小时,大汉突然下车了,让我郁闷不已。
我们的班车司机一路开的飞快,虽然是金杯车,但只要有可能,连警车也会超。藏族大汉下车后没开多久前面突然堵车了,我们司机毫不犹豫的一打方向盘,从对面车道超了上去,才开了10秒钟就看到前面是公路警在临捡,怪不得堵住了。而对面的车因为我们占用了车道被堵得直按喇叭,两个公路警很不理解的走到我们司机跟前,他们搞不懂这车为什么会当着他们的面违章,“你违章变道了,请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公路警是汉族。我们司机很诚恳的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是你们在前头把路堵着。”我差点笑出声来,却突然听到其他乘客也纷纷替司机圆场:“是啊,是啊,我们都不知道你们在前面,平时这里是没人的。”终于,我忍不住笑翻了。
凤凰
结束一个人的旅行是从凤凰坚定的说“明天我跟你走”开始的。这事多少有点突然,八一渡口青年旅舍8人间的寝室里大家聊着各自的行程,之前我知道凤凰是跟着其他三个人一起从成都包车走南线到拉萨的,而且和同伴们相处愉快。所以,当她在床上仰起身对我说“明天我跟你走”时,我还以为她只是随便说说。
“你真跟我走?我挺省的,一路上会比较辛苦,也许会从派乡走着去直白。”我的话简直是在劝退。
“太好了,这一路把我憋坏了,一直没有机会自虐。”她的语境背后透着兴奋。果然,24小时后她走得很爽很开心,而我走得很挫很疲惫。
凤凰和我是搭一辆黑车去的派乡,这辆小奥拓的票价和班车一样,后排只座我和凤凰,还算舒服。前排是一位去派乡干活的四川大哥,派乡到直白的路正是他们公司修的。也正因为修了路,派乡设了个所谓的雅鲁藏布江门票收费站,一个人要150大洋。如此不合理的收费我们当然不愿给,便和司机一拍即合决定逃票(成功后给她一点好处费),四川大哥更是很热心的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于是我脱掉冲锋衣,上身着快干衣,下身破破烂烂的牛仔裤,成了建筑公司总部派来视察的工程师,和四川大哥勾肩搭背、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而凤凰穿上了女司机的外套,成了去派乡探亲的“村姑”,也很顺利的混了进去。
我们加了点钱让女司机送我们到观景台,顺便也把四川大哥送到他的工地。南迦巴瓦云雾缭绕,观景台上啥也看不见,我们背起包往直白村走去。路过四川大哥工棚的时候我们像老朋友般地跟他打招呼,四川大哥乐呵呵的跟他的工友们介绍着我们,灿烂的笑容仿佛把南迦巴瓦前的云雾也吹散不少。
我以为从观景台到直白村一路都是下坡,谁知道这段路高高低低,一会下一会上。二个小时后我走得累死累活,凤凰却走得容光焕发。半路上我们还从公路下到雅鲁藏布江边上,从雅江底下爬上来后,我再也坚持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狂喘,凤凰很同情地看着我说:“把你的大包给我吧,我还好。”虽然我喘得根本不想说话,但事关面子,还是硬憋着口气说道:“没关系,休息一会就好。”
从观景台到直白村我们走了近4个小时,当我爬上直白村唯一旅馆的2楼时,真想躺倒在床上睡到第二天。凤凰却依旧活力十足的样子:“时间还早,我们到村里去随便走走吧。”一个小时后我确信凤凰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孩子,因为我看见前面的雅江第一湾了,那本来是我们明天半天的行程,被凤凰“随便走走”就走到了。看到我筋疲力尽的样子,凤凰略带抱歉的对我笑笑:“不好意思啊,我走的开心就刹不住了。”后来聊天得知凤凰几乎每周都跟济南某户外俱乐部去爬山,基本上已经到了无虐不欢的地步,作为领队上个月还刚去过太白山。我们在第一湾休息了好一会,准备起身返回的时候凤凰吞吞吐吐的问道:“我们能再往前走一点吗?听说加拉村就在前面不远诶。”出来之前我做过功课,加拉村离第一湾24公里,至少6-7小时。那一刹那,我都有了跳雅江的心了。
还好我没跳雅江,我们也没有走到加拉村,否则,我们两个都会深深后悔一辈子的。
回到旅馆,院子里多了几辆越野车,一些专业设备正在不断搬下来,老板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风景摄制组,来这拍南迦巴瓦的日出日落,今天已经第十天了,一直没等到。等我们洗完脸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摄制组已经长枪短跑全部摆好,南迦巴瓦还是云雾蔽日,时间已经快晚上7点了。我们坐在饭厅里正点菜,外面忽然一阵骚动,跑出去一看就呆了,南迦巴瓦前面的云已经散了,一座棱角分明的金黄色山峰就这么不真实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像是看海市蜃楼又像是经历一场梦境般看着眼前这座云中的天堂。我的人品真有那么好吗?要知道这是我在直白唯一的一晚,就让我看到了别人等了一个星期都没看到的南迦巴瓦落日?看来我要对自己的人品重新评估了。
我们在院子里呆了两、三分钟终于反应过来拍照这回事,冲回二楼拿相机,发现二楼拍摄角度更好些,确切的说是躺在床上拍摄的角度更好些。整个落日时间不过二十分钟,等我把相机放回包里的时候发现手机上有两条短信,一看时间是十分钟前的,一条是去新疆的OO,一条是去贵州的小熊,内容都是显摆她们去的地方有多好,若在平时也就算了,现在给我发这个算是撞枪口上了,毫不犹豫的回信:躺在直白农庄般旅馆的床上看南迦巴瓦如梦如幻金色落日,并有一美女相伴。不到一分钟就收到小熊真挚而热情的回复:孙子!

唉,我一点都没骗她们,包括农庄旅馆。这个农家乐旅馆有一个硕大的院子,从饭厅走到外面的门要走7-8分钟,中间还要过一座小桥,桥下流淌的清澈小河就是我们洗漱的地方。住的房屋后面还养了很多动物,猫狗牛羊马鸡鸭都是普通的,至于孔雀,恐怕需要一点想象力了。
第二天上午我和凤凰又在外面走了不少路,所以等到下午要离开的时候我有些犯愁了,再让我背大包走6-7小时真的有点够呛了。可我们等了快2个小时了,一辆愿意回派乡的车都没有,凤凰必须今天回到八一,否则就赶不上火车和公司的上班时间了。我咬咬牙决定边往外走边找车,看来我们的好运气没在昨天傍晚全部用完,还没到村口就看见一辆满载人的卡车往我们的旅馆开去。赶紧三步并两步回到旅馆,等卡车后面的防护板打开我就傻了,还以为是附近村民呢,居然是一卡车穿冲锋衣的游客。这还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一卡车天南海北的人都是在派乡才认识的,而且被一个叫“唐僧”的人鼓动后都决定徒步墨脱。一卡车的冲锋衣徒步墨脱该是怎样的景象啊。
凤凰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子,除了听到“墨脱”这两个字的时候。据说徒步墨脱是她的梦想,据说这次因为找不到伴而同墨脱两次擦肩而过。在对墨脱彻底死心后来了直白村,却在这里碰到这么一大帮去墨脱的人。
唐僧显然是个不靠谱的人,否则这一卡车人根本就不该来直白村,因为唐僧告诉他们只有直白村才能看到南迦巴瓦。事实上直白村和半路的观景台只是角度不同,但那么厚的云,什么角度也不可能看到,这车简直就是专程来接我和凤凰的。当唐僧不厌其烦的告诉每一个人到了直白村,车费变成20元/人,并强调车费由他统一收取,不要直接给司机的时候,我真搞不懂这一卡车的人怎么就能放心让他带队走墨脱呢?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拜唐僧所赐花了20元就顺利的回到派乡。虽然回八一的最后一班班车已经开走,但我们好运依旧,不久就搭到一辆放空回去的面包车,司机是一个虔诚的回族人。在车上凤凰好奇的问我:“你说唐僧真的会带他们去墨脱吗?”“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旅途中总有一些儿奇怪的事和一些奇怪的人是无法想象和预料的”。是的,现在我就绝不会想到第二天早上还会坐上现在这辆面包车,继续我的旅行。事实上当时我连晚上住哪儿都不知道。
想想和休哥
一般碰到陌生人只有别人对我年龄感兴趣的份,我很少去猜别人的年龄,但想想是个例外。想想永远扎着两个晃啊晃的小辫,说话的时候总是四十五度角仰头望着别人,身上穿着老远就能一眼看到的鲜艳衣服。虽然有这些迷惑人的外表,但想想在她的小宇宙偶尔爆发的时候,是个很有老大气质的人。
回到八一我和凤凰仍旧选择了渡口青年旅舍,前台又把我们安排进了那个8人间。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正好碰到想想的小宇宙在爆发,现在已经有5个人跟她明天一起包车去鲁朗和波密了,“明天鲁朗和波密你去吗?”想想四十五度角仰头望着我问道。“我参加,老大!”从踏进房间到定下明天的行程我只用了30秒,这段路风景不错,搭班车不能停下来拍照看景,所以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不要叫我老大”想想很认真的对我说:“叫我想想姐姐。”这是想想老大气质的副产品,一路上她管谁都让叫姐姐。
想想姐姐在问别人包车司机的信息,我随手把刚才回族司机给的名片塞给了她,便跟凤凰出去找吃的,我们还是10个小时前爬山时候吃的一点干粮,下楼的时候腿都有点打漂了。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想想兴高采烈的告诉我,我的回族司机是价格最低的,明天包他的车走。我茫然的点点头,今天回来路上太累了,上车没多久就睡着了,一直睡到八一,给钱的时候都迷迷糊糊的,连司机师傅长什么模样我也不记得了。
第二天早上先跟凤凰在旅馆门口告别,她要往西走,她的同伴们和回程票都在拉萨等着她;我要往东走,川藏线上八一是我的第一站。
我们一车7人都对回族师傅安全第一的开车原则称赞有加,他也一直很骄傲的把安全第一时常挂在嘴边。直到我们的面包车被一辆农用三轮车超过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扬起身看了一眼码表,20码!后来坐在副驾壮硕的北京小伙信誓旦旦的认为是码表有问题,因为在下坡最快的时候我们的车也只到过40码,“你昨天回来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想想姐姐问我,我依旧茫然,看来我昨晚睡的不是一般的沉。想想姐姐摆出标志性的四十五度角:“你昨晚到底是睡过去了还是昏过去了?”
回族师傅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所以在下午5点不到的时候,我们的车突然停了下来,回族师傅变戏法般的变出了白色的伊斯兰教袍、帽子,还有一块用来下跪的毯子,以及其他一些零碎东西。一天五次祷告时间到了,他选了个面向麦加的山坡,开始祷告。两边都没什么特别的风景,我们7个人就在山坡下游弋,清一色的带着墨镜,这时候如果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路过,肯定会以为是黑社会正在办事。
祷告带给我们回族师傅无比的力量,当前面遇到一个很深的积水坑的时候,回族师傅用石块试探了下深度后,很豪迈的大手一挥,冲!回族师傅担心车太沉,让一半人下来先走过去。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我们面包车的发动机传出马达高速运转的声音,在冲过水坑的一刹那,壮硕的北京小伙没有坐在副驾位置,而我看到了码表的指针。后来我用很沉痛的语气把真相告诉了北京小伙:“其实咱们车上的码表没问题,根据种种迹象,很可能是你的体重问题。”
一路上挺顺利的,坊间盛传很危险的通麦天险,除了有段坡太陡,推了次车外,既没惊也没险的过了。到波密已经是晚上8点了,240公里路我们走了一天。波密的晚饭是我们7个人的第一顿晚饭,却也是最后一顿,其中4个人明天要折返八一。一个人的旅行就是这样,每天都可能面对告别,这让人有些伤感,特别是想到以后再也没机会拿北京小伙的体重来开玩笑了。
有失也有得,在和一些朋友告别的同时,也不断有新的朋友加入。波密的饭桌上其实有8个人,想想为我们大家介绍了她的朋友――休哥。想想介绍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丁点老大气质,而是带着羡慕和敬仰的口吻:“他昨天刚从墨脱出来。”当休哥在介绍徒步墨脱的时候,想想很激动地追问着每一个细节。后来我才知道,想想的墨脱情结比凤凰更强更浓烈。
如果一切顺利,想想应该比休哥更早完成墨脱的徒步。但她选错了队伍,更确切的说,选错了老大。根据想想的描述,这支徒步队伍的带头大哥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上至成都军区,下至派乡乡政府,没有他搞不定的,而他自己又去过很多人迹罕至的地方,爬过很高的雪山。当然,每次说这些的时候,身边都有好几个充满崇敬眼神的队员们围着他。
想想是走到松林口被拦下来的,那是徒步第一天的中午,她缺一个户籍所在派出所的证明材料,显然带头大哥并没有提醒和确认她是否有这份材料了。现在只能等户籍所在派出所发传真过来了,松林口的武警战士很和气的告诉想想:“这份材料一定要的,否则就算你过了我们这关,后面还有三个检查站,他们连传真机都没有,到时候你走的冤枉路更多。”
想想一直没有告诉我们带头大哥将她抛弃的具体过程,反正这位认识成都军区的带头大哥既搞不定一张证明材料,又不愿意等想想,所以想想和一起从广东来的一个朋友当天下午就返回了派乡等材料。她们两个在派乡等了三天,每天打电话到松林口,但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份材料最终也没等来。
讲到墨脱,最让想想难过的不是自己没能完成徒步,而是连累了那位朋友,她的这个朋友返回八一后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要去徒步墨脱,便留在八一继续找队伍。在波密的时候,有一天想想突然对我说:“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没跟上这个带头大哥也未必是件坏事。”这次想想没有摆出标志性的四十五度,而是直视远方:“她现在也许找到了更可靠的队伍,你说呢?”我点头表示同意,心里替想想感到高兴,看来压在她身上沉重的墨脱情结总算放下些来了。
我们四个人在波密呆了整整三天,除了想想和休哥,还有个叫菲菲的女孩子。俗话说男女搭配,呆着不闷,虽然三天中只去了趟岗乡,但整天吃吃喝喝、打打闹闹,倒也不觉得无聊。休哥决定和想想包车去成都,有很多走川藏线的车送客人到拉萨后是空车回成都的,所以费用很便宜,折合一个人才几百元。我很想去米堆冰川,休哥和想想也有这想法,但菲菲不想去,所以第三天傍晚的时候她一个人搭车直接去了然乌,顺便帮我们先看看住宿和吃饭环境。
休哥很顺利的找到了车,但他显然不善于讨价还价,因为想想之后随便问了下回成都的价格,几乎比休哥便宜了一半。所以第三天早上我是被想想很没有老大气质、带着央求的声音吵醒的:“去把你那车退了吧,省下的钱够我们在成都大吃大喝好几天呢。”休哥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不好退,这个是朋友帮忙找的,都定好了,我怎么跟人交代?”
当想想知道我也站在休哥一边的时候,耍起了小性子:“那你们两个正人君子去成都吧,我这个小人不去了!”“我要回拉萨的,机票都买好了”我解释道:“再说两个君子搭伴很无聊的,一个君子一个小人才好玩嘛。”说归说,第二天早上想想还是十二万分不愿意的上了休哥的包车。
我不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去米堆冰川,但和我同机回上海的一个女孩子她也去了,只比我早一天。更神奇的是,在她的米堆照片中拍了一个她也不认识的家伙牵着条狗狗,而这个家伙7年前曾和我一起徒步怒江,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联系。如果我能早一天去米堆,就能感受到上帝他老人家的奇妙安排,现在,我只能感受到他老人家对我们的小小捉弄。
从米堆出来,我们当天赶到了然乌同菲菲汇合。在这里我要同想想和休哥分手了,他们跟着包车去成都,而我的假期快结束了,要回拉萨,菲菲也要回拉萨,她决定去尼泊尔。
菲菲
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正坐在渡口青年旅馆8人间的床边整理着大包,整个8人间只有我对面的下铺有一个女孩子蜷缩在床上,床上铺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有一袋卤菜,地上是一罐拉萨啤酒。起初她还一口酒、一口菜,后来菜越吃越少,酒越喝越多。再后来我隐约听到抽泣的声音,她已经不再吃菜,手里拿着啤酒,头埋得很低。再后来她开始打起酒嗝,抽泣声也越来越响。我想,她是不是失恋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菲菲。我已经无法再从容的呆在房间里,下面的布告栏有不少出行信息,我正看着,脸和眼都红红的菲菲过来帖了张纸条,看到上面的行程和我的差不多,便上去搭讪:“你也要去波密啊?”“上面不都写了吗?还问!”这是菲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从然乌回波密的路上我终于忍不住问起她当天的情形,那时候我们已经比较熟了。她想了半天回答我:“我没伤心啊,卤菜和啤酒都挺不错的,后来鼻炎犯了,鼻涕流得厉害。再后来酒劲上来了,就不想跟别人说话了。”
在我遇到菲菲犯鼻炎的时候,她已经在八一呆了好几天了。菲菲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11点起床,然后早午饭。下午出去逛一圈,当然不是什么景点,一般是视察八一的市容市貌,晚饭后回到旅馆,写写日记、聊聊天,12点左右睡觉。一个地方呆够了,就去下一个地方。她在八一呆了一个多星期,只去过边上的一个樟树公园。回想以前自己辞职出去玩,虽然穷的只剩时间,却没也像她这样奢侈的挥霍过。
菲菲跟我们一起波密主要是被鲁朗的石锅鸡打动了,炖鸡用的石锅是用一种叫做“皂石”的云母石砍制而成,而这种云母只有墨脱才有,所以每一个石锅都是从墨脱背出来的。主要食材是山野放养的本地土鸡和手掌参,乳白色的鸡汤里翻滚着鸡肉,咕嘟咕嘟的冒着香气,这种场面想不抢着吃都难。一个石锅适合3-4个人吃,所以我们分了两桌。想想还在那瞎客套:“大家赶紧吃吧。”,在想想说完那个“吧”字的时候,菲菲已经把第一块鸡肉咽了下去,看来味道确实不错,她的眉头满意的舒展开来,手上却不停歇,右手夹起第二块鸡,左手拿勺装了满满的一碗鸡汤和手掌参。看来今天遇到高手了,动作麻利、频率迅速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她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说,我发现我选错了桌。
当我们起身买单时,菲菲正从石锅里倒出最后一碗汤汁。“厄!”菲菲在喝完最后一口鸡汤后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然后略带愧疚的对我们笑道:“今天中午吃的有点多。”我想“有点多”是个谦虚的说法,你只要看看隔壁那桌还剩半锅鸡汤,里面还有剩余的鸡和手掌参,就知道她有多谦虚了。我忘了说了,3-4人的量是按照藏族同胞的胃口来算的。

没有冲锋衣,也没快干衣、登山鞋或头巾什么的,梳着马尾辫的菲菲永远穿着件不显脏的黑色滑雪衫,背着个普通的双肩包和一个单肩大布袋,布袋上的拉链还是她自己装的。菲菲的相机是家乐福买的已经停产很久的柯达胶片傻瓜机。“照片冲出的效果对得起价钱。”菲菲评价她的相机:“才49块钱,还送2卷胶卷。”
在拉萨吃盖浇饭的时候,菲菲对满大街的冲锋衣们有些困惑:“你说又不是去爬雪山、进墨脱什么的,有必要非得穿着冲锋衣、蹬着登山鞋、拄着登山杖、背着硕大的包吗?”不等我回答菲菲接着说:“最奇怪的是有些人一穿上这些行头,眼睛也会跟着移到头顶上去,像我这样出来旅游的在他们眼里反而成了另类了。”我笑着说:“我觉得你这样挺好,很自然。”“我也觉得自己这样挺好的。”菲菲说:“你说他们这算什么呀?”我看了一眼自己的登山鞋:“装B”。
也许是毛细血管比较发达的缘故,菲菲很容易脸红,喝一点酒的时候、吃完一大锅石锅鸡的时候,还有,当聊到鼻屎等恶心话题的时候。不要理解错了,她是开心而兴奋地脸红,据说这是除了八卦以外她最有兴趣的一类话题。还好,多年的交友不慎让我这方面的抵抗力已大大超越常人,一路上只苦了想想她们。当想想和休哥在然乌和我们告别后,我们搭顺风车回波密,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菲菲显然找到了聊这类话题的好时机,我的抵抗力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不过此类话题注定是短命的,因为我们的司机快受不了。“换个话题吧,”我的语气很诚恳:“司机师傅出来挣个辛苦钱也不容易啊。”
跟菲菲混熟后才得知我俩居然还是老乡――上海人,“我一般不告诉别人我是哪里的”菲菲说“免的一会又要你们上海人怎么怎么,无聊。”“是挺无聊的”我说:“最无聊的是说我不像上海人来表扬我。”我们聊天一直保持用普通话,哪怕只有我们俩人的时候,不主要的原因是这一路上大家都习惯了,主要原因是说到那些让她兴奋地话题时,我们的上海方言都显得捉襟见肘,没有普通话那样酣畅淋漓。
回到八一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就赶回了拉萨,因为得知前一天那曲地震,拉萨也晃了好几晃,这种热闹我们居然给错过了。所以想早点回拉萨,看看有没有可能赶上余震。回拉萨当晚我们把无穷的懊恼化成悲愤的食量,先吃了大盘鸡,又去弄堂里吃了烤羊肉和超赞的烤羊蹄,吃完烧烤,我们腆着肚子踱回北京东路。刚到路口我们就傻眼了,整个北京东路两侧站满了人,每个弄堂口更是不断有人涌出,街上武装巡逻车一辆接着一辆,荷枪实弹巡街武警一队接着一队,每一个街口和弄口都至少有七、八个手持盾牌的武警极力维持着秩序。骚乱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一看没有打砸抢烧啊,再一问路人,刚才有强余震。我和菲菲对看了一眼,感情我们两个都是死人啊,怎么半点感觉也没有?难道烧烤摊的避震系统特别好?还是在我们溜达回来的路上发生的,只有一些老房子有震感?反正那晚我们在马路上站了三小时也没弄明白。当然,站三小时的本意是想看看还有什么热闹,但越看越无聊,最后我都能测算下一辆经过面前的武装巡逻车的车牌了,就像《楚门的世界》里的场面。
百无聊赖中给朋友们发短信通报遇到余震,在上海留守的回复我“恭喜你,又完整了”,嗯,真了解我;贵州那帮孙子回复我“又不严重,手机通讯还正常”,比我还唯恐天下不乱;新疆那帮人回复我:“牛啥,我们喀什也地震了!”,算你们狠!对于没有感受到余震,菲菲也陷入到深深的懊恼中,主要表现为自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聊过让她兴奋的话题。当然,事实上回到拉萨后的第三天,菲菲踏上了前往尼泊尔的旅程。
菲菲的英语不是很好,很多时候还不如我这个英语盲,她去尼泊尔的信心来自于她丰富的词汇量,确切的说是骂人和脏话的词汇量,她掌握的近百个专业词汇中我只听说过十来个。菲菲承认自己有“被害妄想症”,所以学了这一堆专业词汇以防身用。我告诉她去尼泊尔只要注意男性口头骚扰就可以了,一般不会有实质性的行动。但她不放心,自己琢磨了一套防身八法,除了遇到口头骚扰用专业词汇回击外,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回到旅馆第一件是检查床底、衣橱和浴室有没有人藏着。后来和她聊天得知,在尼泊尔,她一直忠诚的执行了这八条。并且因为“被害妄想症”,闹出了不少误会和笑话,最夸张的一次博卡拉Lake Side半条主街上的人都被她惊动。
十月拉萨的早晨阳光明媚,菲菲把布包寄存在前台,背着双肩包去西站坐前往日喀则的班车,菲菲不让我送,我借口出去吃早饭陪她到了公交车站。这才注意到菲菲鼻子红红的,看来她的鼻炎又犯了。车很快来了,她同我摆摆手跳上了公交车,远远看着她在公交车上使劲抽着鼻涕,又想起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车已远去,抽泣声犹在耳边。
后记
相比川藏线上那些著名的故事,我想我的故事既不算特别有趣,更和轰轰烈烈沾不上边。但不管我们曾经在这条路上翻过多高的垭口,转过多少神山,最终翻过和转过的,还是自己心里的那一座山,这就够了。仅以此片裹脚布献给所有曾经和我一路同行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