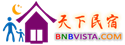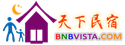镜头一:南航广州-乌市航班,一汉族中年男上躯微微前倾,向下朝着一个维族中年男开口:“excuse me”……
镜头二:和田,6路车站附近,一大一小两个维族小孩呼啸着掠过身边,其中一个回头向我问好:“hello”……
镜头三:吐鲁蕃,亚尔乡村道上,漂亮的维族妈妈带着更漂亮的少年和我擦肩,微笑,少年张口对我说:“how are u? what’s your name?”
从踏上喀什的土地开始,脑子里的疑窦就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深。
飞机上旁听到的对话代表了许多内陆汉人对南疆的全部认识,前座的一对出公差的中年男一登机就忙着向邻座一个喀什本地汉人打听,究竟那个神秘的地方是不是如传说中一样慓駻而危险。新闻时不时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是这样,印象中,喀什上新闻的机会多数都跟负面事件相连,以至于普通的南疆人都变得面貎可疑,再加上距内陆腹地几千公里的物理距离,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只会在电视新闻上偶尔瞟到几眼关于它的消息,就像端坐在电视机跟前,欣赏伊拉克的炮火一样,过后还要品评一下炮火跟烟火区别到底有多大。
一到喀什,汉人中的大眼睛们就会气焰全消,因为在这里,无论性别年纪,任谁都有一双足以睥睨群雄的大眼睛,还一定都是配上高鼻和长睫毛。
喀什古城里担当讲解工作的姑娘很骄傲于她自学成才的多种语言能力,虽然书念得不多,但除了母语以外,还学会了英文、日文和汉语。当天同行的是韩国人郑老师,他的中文几能乱真,所以平时主要担任涉外讲解员的古丽姑娘必须要调频到中文频道,这对她来说似乎有点困难,因为不时会从她嘴里蹦出英文字母,还常常脱口而出ENGLISH PEOPLE ……, BUT CHINESE这样的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