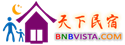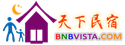出发前,朋友们很理性地告诉我,在环境如此被破坏的现今,大片的草原已经很难看到了,我很理性地点头称是。只是遐想中的内蒙古,是合该应着那首诗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般如诗如画的美好场景,在我心中情不自禁地一次又一次地描绘着,那片接天碧绿的诱惑一次又一次地放大着,光是这样的想象就让我沉醉了。于是,不禁还是满怀着憧憬踏上了旅程。
期盼中的等待总是格外地漫长,纵使我依然试图让自己平和如昔。只是心中还是有丝雀跃。到了内蒙古的第二天清晨,我拉开窗帘,极目向天际望去。虽然天还未透亮,但是我的确失望了。接天的不是碧绿,而是一片蒙蒙的黄,是沙漠。对比着古诗,有些对人类的感喟和不禁油然而生的悲凉。但是在感慨中所没想到的是,和沙漠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却来得那么喜出望外。
那天中午,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杀到了当地极富盛名的响沙湾。响沙湾,顾名思义就是能发出响声的沙漠。至于为何能发出响声,有人说那是指坐在沙顶向下滑,会发出轰鸣声;也有人说是因为把沙子握在手里攥紧会发出哗哗的声音。我带着不解和新奇走下了车,风夹着沙迎面而来。不若江南柔软的吹面不寒杨柳风,沙漠的风天生就是如此不羁和张狂。我迎风而立,望着从脚下绵延至天际的沙漠,顿时心中一片澄黄。不论是因人类而衍生出沙漠,还是沙漠先于人类而存在,那般无际的广袤让人震撼,让我倍感渺小。我无法形容心中的感觉,只能再一次折服于自然的神奇,也似乎懂得了古人为何面对自然时多了那几分由衷地膜拜。
小时候,读不懂三毛的撒哈拉故事,却因为那记住了沙漠的寂寞。而在那一天,当自己站在沙漠中时,却觉得沙漠寂寞但也不寂寞。沙漠只有一个永恒的主色调,我不知道它是否有四季般的性情。沙漠中也有植物,那些植物没有沁润的翠绿,它们的绿浓重得接近于黑。我固执地认为它们是绿的。因为绿意味着生机,绿给寂寞带来了希望。沙漠中还有一种小小的,圆圆的黑色甲虫,不知道那是什么,只见他们如飞般在沙中刨挖着,不一会黑色的身躯就消失了。想起电影《The mummy》中,也是如此的黑虫在守卫着那方神圣。或许这里的黑虫也是在守卫着这片沙漠,他们的家园。初识沙漠,我莫名地被感染了,甚至如孩子般地新奇和喜悦。
其实不止我,很多朋友仿佛都回到了童年无忧无虑的年代。他们(不管是成年还是未成年的)都纷纷脱下了鞋,尽情在沙漠上跑啊跳啊。而我也是,笑着喊着跳着舞着,极孩子气地。我不禁在想,对于我们这样的旅客,沙漠是不是有种母亲对待孩子般的纵容?有一个极可爱的小女生,光着小脚丫怯怯地在沙漠中寻着别人留下的脚印慢慢前行,不一会就蜷起脚指头抬起头很沮丧地对我说,沙子太烫了而且有好多小虫子,不敢走了。那种神情让我想起了自己儿时的胆怯和那些小小的尝试,带着回忆和现实交融的快乐,帮她把鞋穿上了,还忍不住香了她一口。还有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偷偷地朝我踢起了沙,而我立刻欢乐地反击起来,笑着闹着,于是有了那张捉对厮杀的照片。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那个寂寞的童年时代,那一刻我真的以为我拥有了纯粹的欢乐和童年。
最后,我还是没敢从沙顶往下滑,因为心中还是有一个没有长大的胆小的小女孩,勇气的积累远远比不上人的成长。但是在现场的感觉还是让我不禁觉得响沙湾的响沙名副其实,从沙子上滑下来的声音让我联想到古时沙场征战的场景,那时想是厮杀声、风声与沙鸣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吧。
离去的时候,有些不舍。今昔一别,下回再见不知又是何年?试着装一些沙子回去,却因为没有容器而作罢,那就一切随自己的心意。也许是故意给自己留一些遗憾,这又何尝不是给自己多留了一些回忆和期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