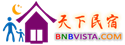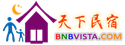LEVI说任何旅行都应该有三个维度来记录,时间、空间和社会阶层关系,就是这样,把一个人身上原有的连接线暂时切断,赤裸裸地放置在另一个三维空间里,这种旅行会随时让你变成另一个人。

一个喜欢汽车、火车、轮船,做长途跋涉的人,又同时喜欢浮皮撩草,吹弹可破的人间关系。轻与重轮番登场,在我的旅程中不厌烦地做着跷跷板游戏。我一边对因偶遇而引发的电光火石背后所凝聚的能量顶礼膜拜,一边在每次留下联络方式的笔迹还未干时就忙不迭地质疑,这不过又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速溶符号。有时候我想确切地测量自己究竟能有多残酷,有时候又会为一秒钟里展现出的多情和真正的善良而疑惑。
无论是哪段旅途,于我来说,它们最后都简化成一幅幅人物素描。但凡回想起,总是只有哪几个让我开心过,伤心过,烦恼过,喜欢过,恶劣对待过的人跳脱于层层叠叠的回忆之外,提醒着曾有过什么样的时间从我脚下向后退远。
终于承认我是一个多么吝啬的持机者,每次转身后都有巨大的后悔涌来,而每当取景框工作时,又总是轻易让喜欢的脸溜走。
沉默的十六岁
把石头房子搭在路边的一队克尔柯孜人还没学会如何向游人兜售自制的小商品,所以他们即便生活在交通要道上,也没能利用它给四壁空空的石屋添几件像样的家什。我们无法交流,只能四目相对地傻笑,他们没有对镜头表示异议,但也无法留给我们一个可以寄达的地址。一群人里只有一个16岁的小姑娘还可以告诉我们,她16岁了,然而除此之外,甚至都无法从她嘴里问出学校在哪儿。她的16岁,眼角已经爬上好多条清晰的皱纹,即便如此,都无法掩盖她日日与阳光直面的美丽。
喀什城里的小孩子早就对游客见惯不怪了,拍了照片要争着看看是必须的,一不留神直接把相机都接管了也是可能的。一家五口挤在窄小天井里古丽已经知道招徕游客帮补家用,她让2岁半的妹妹站在家里唯一的床铺上为我们跳舞,深知没人可以拒绝可爱的小孩,就算是要为此付出20块。她自己的舞姿比妹妹专业得多,她的手势柔软,患有眼疾的左眼因刻意躲闪而更令人迷惑。她并不能回答我们关于这个家庭这条街巷的问题,只是反复说着相同的主题,我没有学上了,爸爸也没有工作。
帕米尔高原的爱情
为什么这么热衷出行呢?新添的答案选项是,只有在旅途中,我可以假装成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众情人。这一趟,不仅收获到来自海拔将近5000米的表白,还在卡拉库里湖遇到马夫的求婚,如此完美的体验,对于一个只当过各种品牌粉丝,从没尝过万人迷甜头的家伙来说,怎么可能不一念再念。
就像“姑娘”是创作型歌手永恒的母题一样,常年因活动半径不大,垂直海拔倒挺大所限的小伙子把找个姑娘谈恋爱当作主要梦想是多么正常的现象,只是,稀薄的空气不足以培养出锐利的眼光,所以缺少挑姑娘的眼光也是理所当然。来自日照的小家伙对那个叫“外面”的世界有掩不住的好奇,常年被雪山冷藏保鲜的一颗心,实在太容易被偶然间的一阵高热灼出滋滋的响声。
至于卡湖的求婚辞是这样的,这名前缀颇长的25岁疆大应届毕业生,趁着暑假还未正式上岗的克族中学老师,牵马赚外快的临时马夫对我说,你毕业后来喀什吧,这里工作好找,然后我们就结婚。连祈使句式、感叹词都能省下的求婚应该算酷吧,而且在一个短句里把面包和爱情都考虑到了,可见是理性与感性兼备的人才,于是我禁不住暗爽到内伤,满心欢喜地花十块钱骑着小白马在卡湖边得意地笑。
马不停蹄的韩国人
假如我在20年前已是现在这把年纪,还恰好有足够的盘缠去观赏祖国河山的话,遇到最多的亚洲友邦人士应该是日本人吗?不需要更多的逻辑学知识,以我这种智能也能推算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现在,踏着欧美人、日本人踩出的道路,韩国人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关于这一点,看看灵隐寺新增的韩文指路牌,城市里激增的韩语学校就可略知一二,更别说电视里播不完的韩剧,虽然他们都被同样几个配音演员给中国化了,但还是货真价实的泡菜味进口货呀。
釜山来的郑教授慢条斯理地讲话方式一度把我们都蒙敝了,验明正身后还止不住怀疑,真是外国人吗?跟高芭她们分开后,芝麻同学和教授先生被送作堆,这才有了愉快的喀什一日游行程,曾分别在台湾和南京念中文的教授先生用一天的实际行动一扫我的“恐师症”。话说自打青春期开始就不怎么招老师待见的芝麻,一向与老师们保持着可敬的距离,既提不出有见地的问题,也拍不出有声响的马屁,这样的情形在遇到郑先生以后小有改观,因为旅行总是有本事让人变成别人吗。
虽然不能认同教授先生“大家都是读书人”的断语,大家还是在相当友好、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对话。不仅谈到了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韩星和韩国综艺节目,教授先生还特别贡献了在海滩偶遇苏志燮的独家花絮供我遐想,我们也上升到理论高度,由他向我传授了点论文选题技巧,当然,间中也让我再次证实了排骨在韩国的身价的确不菲。
当天深夜,与教授先生在毛爷爷挥手的雕像前分手时我并不知道,接下来出场的旅伴仍然是韩半岛来客,而且,从此开始,我的生活品质将急转直下。那天晚上,我的胃里填满了体贴的教授先生请吃的昂贵维族菜,根本想象不出一天只吃一顿面是什么样子。
从看到行李箱里的巨型背包起,我就在大巴上默默搜索那个可能是同好的家伙,无奈眼前没有出现足够一亮的面孔。等车到了和田汽车站,才在售票处发现背包的主人,一个留着山羊胡子,明显营养不良的瘦家伙,顿时决定不搭讪,先走为上,谁让我对胡须男一向缺乏好感呢。哪料到有缘千里来相会说的正是下面这一出,当我看好床铺,准备交钱住下时,该名男同学适时出现在前台,要求看看这里的床铺长什么样,偷懒的服务员直截了当让我担任导览人员,带上他去参观。
金明浩同学自此正式登场。他从红旗拉甫跨国境归来中国,说归来是因为他的环亚旅行是从中国开始的,这个长年休学旅行,穿上古装,胡子都不用粘,可以直接去演《大长今》的家伙迄今为止还只是一名大三生而已。第一顿沉闷的晚饭过后,根据他的建议我们买了啤酒回旅舍对饮,原以为这会是个不错的开始,哪料到最初对胡须男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他果然不是理想的旅伴,既没有英俊到令我发花痴,也没有幽默到让我忍不住往下跟,“惜字如金”四个字可以被直接刻在脑门儿上。次日一早我就偷偷溜了出去,打算自己一个人去碰运气,兴许会遇到更有趣的旅伴。等到我在城里蹓跶完一天,被和田的太阳晒蔫掉也没碰到任何一个跟我一样无聊的旅行者而回到旅舍后,邻居金同学来敲门,说一起吃晚饭吧。在这顿稍微活泼的晚餐上,他宣布放弃等待大巴扎的计划,加入我接下来的一小段行程。那么,因为奥运会的原因,因为安全的原因,因为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国际国内原因,2008年夏天,淡的出鸟来的南疆旅游季提供给我一个无法选择的选择,就这样,我们一起上路了。
对于芝麻这种一旦上路,就努力要打造“三贴近”形象的家伙来说,金同学实在是太脱离群众了。我努力到连在沙漠边无名旅舍摸黑刷牙时都还跟风尘仆仆的,满身汗味的洗友大叔攀谈一番,而他呢,连我这个一路同行的亲密战友都舍不得多讲几个字。原以为我真得要像只好奇的斑鸠一样一路靠勇敢地搭讪来填补无聊时间了,金同学的秘密在喝过两瓶啤酒后终于现身了。有些好饮者会在酒精的作用下撬开自己的嘴巴,这个酒量看起来颇有些深的金同学至少要酒过两三巡之后才肯连贯地说话,日后所有关于他的故事也都得借着酒精蒸发出来。而我呢,幸好我对旅伴的态度有如伸缩性极强的变形虫,有兴趣发现任何我没有的趣味,何况,酒啊,我所欲也,用它做媒介去认识一个双子座有什么不好?
当我渐渐习惯了金同学白天黑夜双面人的特性后,我们一起的行程也差不多走到了终点。另两个从昆明辗转而来的韩国人将在吐鲁蕃与我们会合,确切的说,是与他会合。一个是头发胡子一样多的崔前辈,另一个是自然卷,戴发箍的后辈,一个是话痨水瓶座,另一个是比金同学更加沉默寡言的未知座。这样的组合带来一个不随着背景变动的画面,不论是在出租车里,还是烧烤摊前,两个都因为害怕冷场起鸡皮疙瘩的水瓶人不管是不是才刚认识三分钟,就神叨叨地天一句地一句的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