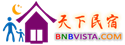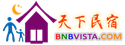我手拿朝芴浑身不自在地站在丹樨之下。假如你有特异功能浮在半空观察我们这些上朝的人,就会发现我实在是个异物。身高一丈九尺,膀大腰圆,獠牙与豹眼占据面部百分之六十的面积的我,偏偏站在文官班列。我得小心呼吸,因为我的肚脐眼紧贴前面大理寺左丞的脖领,而我的屁股则可以遥感到身后翰林院侍读老学士的轻声咳嗽。皇上还没有升殿,武官班列有几个家伙对我吹胡子瞪眼,前天羽林军偏将这个附庸风雅的老粗找我下围棋,输了棋死不认账,被爷爷热烈地“教育”一番后,“心甘情愿”地吞下半盒黑子。
我也不愿意这样傻站在这里。
但谁叫我承袭了老爷子的恩荫,朝议大夫,文官从五品。
像我这样的散官平时是不用上朝的,今天是太子议亲,大贺的日子。
偏偏昨晚吃坏了肚子,腹中的不平之气寻求出路,忍无可忍之余,只好随它去了。
结果就是翰林院侍读老学士当场昏厥,我被左都御史参了一本。老学士的儿子认为堂堂四品大员、翰林学士居然被一屁放倒简直是家门大辱斯文扫地,扬言这事儿没完,准备联合御史台一起给我上纲上线。可惜他忘了,圣上还是藩王的时候,就是我父亲的学生。于是我以“失仪”被罚俸三个月,转杭州观察学政,避避风头。
在满觉陇找到住宿的驿站——江南驿。驿丞对我爱理不理。我这样有品无职浪费纳税人钱帛的散官,到哪儿都不受人待见。管他的,至少房间不错。我要了间上房,窗外就是郁郁青山。屋子里有些凉,春寒清冽地在空气里游荡。巳时未到,午餐尚早,于是决定出去走走。
临行前打赏了驿站小厮,问清了路线。我所在的满觉陇在西湖南麓,遍生桂树,秋天时漫山桂花香,称为“满陇桂雨”。之后的行程,准备是沿山路走到雷锋塔下,往回折一点上苏堤,从苏堤走到孤山,绕曲院风荷,再寻个牛车回客栈。
山路边杉树高大笔直,但是还没有长叶子,低一点的位置山花烂漫,中间则是飘忽不定的绿意。若非官道上车水马龙,这条路本身就是好景致。旁边就是西湖,水天一色,往来士女如织。不长时间就走在雷锋塔下。雷峰塔去年翻新,气派有余,风度不足。稍事瞻仰便原路返回,苏堤才是心头好。
千里相投,我不负苏学士;苏堤春晓,他不负散大夫。路上停留两次,为的是坐在湖边吹吹暖风。当然还有另一层考虑,穿着官便服一阵风似的步出苏堤,会有人以为是钟馗正在执行任务,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从苏堤出来,就有一大群人围了上来,问要不要买着买那。我微笑摇头,可那帮不识相的仍旧不依不饶。爷爷心头火起,大喝一声:“爷就是不买,咋地!”
鼠辈们逃窜的风姿堪比樱花飘落的绚烂。
孤山对我来说不过一小丘。山上有个敬一书院,本着“观察学政”的朝廷旨意,我打算进去看看,可刚到门口,就有几个青衣下仆拦住去路,说是书院已经改成当地缙绅的销金窟,请大人改道云云,说不得,只好怏怏回转。在院前遇到一个在销金窟里快活的阔人,看面相倒有几分书生气。该阔人想是忘形于山水,在水池边高歌不止。
孤山上下来,临近有画展的宣传海报。第一眼看到是画展,不由哼了一声,准备蔑视之。再一看,说是西洋画,仔细又瞄了一眼,发现左下角招贴画里的女模特没穿衣服,于是,咳咳!本官决定去现场支持一下艺术创作……
画展出来又顺道拐进隔壁的浙江博物馆。浙江文化传世,历代巡抚搜罗古物不遗余力。看到了名为“泗州大圣”的雕像,白面书生低眉顺目。这是观音菩萨的变体,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泗州大圣”像。
左逛右逛,日之夕矣。我在木浦处找了茶座,渐渐等它夕阳别湖山。老人家们在打牌,小孩子玩滑板,交通协管指挥着来往车辆,小姑娘叼着片苹果执意让她有点腼腆的小男朋友接过去。就在秋瑾像紧锁眉头大义凛然的时候,一对对新人在她的台阶下绽放。湖面波澜不兴,安静地接纳着轻若无物的花瓣。它这样的安静了千年,每年都有花瓣飘来。在此之前呢?我不想知道,在此之后呢?我不能知道。时间在流转,人在流转,我也在流转。 每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就会忘记我在塞外金戈铁马的日子。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在鹰飞狼奔中寻找我的快乐。匈奴的勇士以我为敌,但也尊敬我是一个战士,在策马边塞田埂的时候,风吹麦浪,收麦的姑娘会向我招手,我对她打个唿哨,看着蝴蝶落在我刀柄上。我幻想着哪天我直捣可汗牙帐,会被一支流箭射中,就这样死去。这样的话我的骏马就会把我拖到世人到不了的地方,夜叉般的我铸就了永远的传奇。可是我没死,我家老爷子死了。嫡出的大哥也因为花柳病去见了老爹,唯一的传人,也就是我接受了恩荫,永远告别了我的骏马和草原,坐在一帮如肺痨病人一样的读书人中间,在阴暗布满灰尘的大厅里学着他们哼哼哈哈。日子在继续,而我,在时间的洪流里流转。
照这样下去,在六十岁的时候我也终究会变成那个样子吧,一个真正的文官。
想到这里我放下了手中的杯子,走过曲院风荷,去找辆牛车。路过了一个什么人的墓,没看清楚。正当我意兴阑珊的往前走的时候,背后忽然阴风惨惨,一个独臂头陀在我身后大叫:“前面莫非是李逵兄弟!想死洒家啦!慢些走!慢些走!”我想起来了,路过的是“大宋义士武松之墓”。
我猛的回身,紧紧抱住惊慌失措的武松幽灵,泪光闪闪,内心是无比的喜悦:说爷爷是文官,他娘的,连鬼都不信咧!
朝议大夫说:浙江博物馆里有常书鸿分馆,在江南和敦煌的保护神不期而遇,也算是意外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