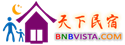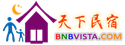在离天堂最近的青藏高原,宗教和信仰简直可以说是藏民的氧气和水,不可或缺。在这片雪域上,信仰之于生命,犹如青稞酒酥油茶之于生活。未到西藏之前,我只在书中略知宗教之一二;去了一趟西藏,我才醒悟什么才是这世上真正的宗教,什么才是虔诚的信仰。
在青海的塔尔寺(黄教六大寺之一),我看见无数的信徒,五体投地磕头膜拜,佛像前的木板被朝拜者的身体磨得深陷下去,油光滑亮的。围绕着大金瓦殿,信徒们沿着顺时针方向或缓步,或急行,或磕着等身长头蠕动,嘴念着六字真言,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倦。在许多沧桑而虔诚的面孔中,我们发现一藏族青年妇女,眼神里跳着祈望的火花,怀里抱着的不足1岁的娃娃,眼巴巴吮着母亲敞开而随步摆动的乳房。她无数次疾步绕行,孩子在怀里睡去,她还在无止尽地走着。那些真诚的足音,整整在我耳畔响了许多天,震摄了我整颗心。
在拉萨的林廓东路边,我们在吃着早餐。在人来车往的街道上,我们亲眼见到一男一女两名藏胞一前一后地磕着长头。他们双手合掌高举过头,然后降至鼻尖,胸口,身体迅速前扑,双臂前伸平放在地上划一记号,全身匍匐,然后起身,跨前两三步到记号处,再重复以上动作。由于前额及鼻尖贴了地,所以其上都有灰土沾成的圆点。他们的藏袍外套着一件帆布长围裙,双手垫着木板。他们一丝不苟,任凭时尚和现代的东西在身边一闪而过,他们的心不为之动,信仰不为之变,我行我素。据说他们中许多人还是从四川、青海、甘肃等地一步一个长头磕到拉萨,历时往往一年或几年,不辞风霜,不辞千里,不惜抛家弃产,沿途乞讨也要到拉萨,所以在拉萨乞讨的人很多。他们往往因朝拜而抛其所有,最后除了信仰便身无分文。这些乞讨的人总令我们敬佩,他们是精神的富者。在八廓街大昭寺前,我们也见到无数磕长头的人和乞讨的信徒。我不想对他们说长道短地评论,但他们的虔诚确实令我感动无言。我心灵所受的悸动,也许并不亚于1818年,白人探险家第一次发现在北极冰雪世界里竟有顽强生活着的爱斯基摩人时的震惊。在这难得真诚、信仰早已支离破碎的后工业时代,我终于看见这世上还有如此纯粹靠信仰而活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身体,一寸寸地丈量着通往终极的无穷路。
在西藏,我们随时可见迎着寒风飘扬的经幡(又名风马旗)。每家屋顶,每个山头山口、河边、树顶、桥上,甚至热闹的街上十字路口,都插有这些代表藏民信仰与崇拜的经幡。据说经幡中的五色,其蓝象征天,其白象征云,其红象征火,其黄象征地,其绿象征水和木。藏民们相信,印满经文和图腾的经幡每飘动一次,就等于向上天传送一次经文和祈祷。因此,每每见到经幡,我都会不由自主竖耳聆听。我不知道苍天在上是否也在倾听,这千万遍经风经雨的祈祷声。
在西藏,人人口中念念有词。他们都在念诵六字真言。整个西藏变成了一个“六字真言”的嘛呢世界。人们走到哪里,都手摇嘛呢筒,转嘛呢轮,绕嘛呢石堆(又名玛尼堆),诵嘛呢咒。就像十九世纪一英国学者所描述的:“在西藏的每个十字路口,每走一步,都有某种形式的六字真言在注视着旅行者”。也许每个西藏的孩子自呱呱坠地时,便在父母的嗡嗡嘛呢声中逐渐学会了唱诵真言,至老也念着六字真言坦然离世。绝大多数的藏民,从早到晚,从生到死,一举一动,无不与他们的宗教和信仰有关。他们的家里大多有一个小佛堂或小小的神龛台,还有酥油灯、哈达,香和八宝吉祥物等供献品,供家人早晚叩拜祈祷。不论男女老少,出门人均配戴“格马”或“松科”等护身符,手不离念珠。念珠都有108颗珠子,不念时绕在左手腕上。西藏宗教节日很多,人们在节日里既娱神也娱人娱己。在藏民眼里,神灵无所不在,每座山每条江每片湖每棵树甚至每个人身上,都有可供朝拜的种种神灵。神山圣湖,寺院古迹,都是朝圣的对象。在民间,有些牧民见佛就拜,见塔就转。在西藏,人们心甘情愿地供养着喇嘛。喇嘛如同汉语里的“和尚”,藏语意即“上人”。人们相信喇嘛是引导他们进入佛道的唯一导师。子女出生要请喇嘛命名,男女婚嫁须请喇嘛占卜,患病要喇嘛医治,人死后要喇嘛念经。在藏传佛教的西藏,喇嘛无论是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格鲁派(黄教),还是本教(黑教)的,都很受普通藏民的尊敬。难怪藏俗语有说:“日月高于山巅,喇嘛高于国王。”在西藏我们遇见无数身披袈裟,面带微笑的喇嘛,其中有一位年逾花甲、须发皆白、慈眉善目的喇嘛,他满面红光,身体健硕,见我们上了车,便主动牵扶我们,一直微笑,欲言又止,我们用眼神笑态交流着一切。我仿佛觉得眼前的他本身就像一尊佛。西藏就是这样,全民信教,人皆好佛。宗教世俗化,世俗宗教化。在藏传佛教影响下,民风纯朴无邪。河畔路边的东西放几天也无人偷,寺院黄金万两也无人盗。他们怕报应、积善果、戒五毒。他们对信仰的虔诚不二,常令我们这些俗人惭愧不及。他们在这世界上最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中,仍对自然感恩戴德,用他们的宗教信仰支撑着整个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