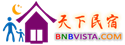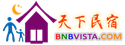前言
过程,也许是一生也许是一瞬。
最近不是流行什么死了都要爱嘛。拿烂人嘴里溜一圈出来就变成死了也要烂。
流行真是一种毒。
烂克某天睡醒了,说:“想着该和咱姐三个再来一次旅行了”。
于是就出事儿了。于是烂鱼说了:“一个都不能少”。
这中间,烂克好容易上岗了。烂鱼不小心下岗了。差点没把烂娃气晕过去。
真TMD不靠谱。
拿烂鱼来说。拼时间拼内力拼财力谁能拼过下岗的啊。说是云南,真扯到西藏也就一念之间。没想到,这真成了预言。烂鱼终究把烂娃和烂克甩了。直接进了藏。Y绝对的烂人!
拿烂克来说。攀枝花的卖身契,凄凄惨惨的签了一年,新房也没落着多睡几天就驻攀办事处了。身在外,走哪不也就一抬脚嘛。
烂娃的反应一直是比较迟钝。老年痴呆症也不是1年2年的名声了。计划着把窝里的尾巴们忽悠去云南,仨再拐道偷偷去色达。让那帮家伙边晒边骂边吃边骂边小资边骂。为了死了都要烂的2007的宗旨,朋友就是拿来出卖的。等那帮家伙反应过来,烂人已经颠在高海拔了。骂吧,尽管骂吧。没信号。
走吧。
成都-马尔康(¥91/人)。出发的那天,肥皂剧看完已经是临晨2点半,五点半就得起床,这点时间还真是倒多不少的。当然,最后还是挣扎着去当猪了。六点半,班车准时离开茶店子。那一车站密密麻麻的背包客啊,散落在各个长途车上,接着将被运往四川的西部。川西的大地又会开满冲锋衣。
还好,我们这挂车上就只有我们仨是背大包的。看来这条线不会太热。
很好。就喜欢人少的地方。数羊也比数人好。
俺没什么嗜好,就爱睡觉,总睡不好。入睡很难,醒来容易,极细微极遥远的声音听起来就象在耳边。当天亮起来,世界开始嘈杂的时候才容易睡去。所以脸上总是痘起痘伏的,从来没有干净过,当然熊猫眼也从来没有消失过。这样长久以往的就成了神经衰弱,也就是说俺那脆弱的神经生病了,简称神经病。
从出发一直睡到中午,一个人坐在后排,旁若无人的猪睡。车屁颠屁颠的在山麓上迂回,断断续续的在睡,断断续续的在醒。下车放水,趁机下车伸了个懒腰,坐在路边樱桃摊抽烟。烂人说我穿的T恤好春哦,我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咧着嘴很的瑟的笑。阳光正好。
下午四点半。马尔康。阳光浓烈,饥肠咕噜。红原酸奶(¥2/杯)真是上瘾。NND,你说我怎么就不带一桶上路呢?真的笨的有点具体。这后面的路上谗的啊,念了一路找了一路。唉。早知道就发了。
马尔康-色达(¥60/人)。色达的票依旧没有着落,包车也没有找到伴。三个人的在街上晃来晃去,追着车问来问去。一点也不着急。都是些什么人啊。只有一个解释。“烂人”。
一大早起来,LK上厕所回屋,给了我三十元钱,说了声:“捡的哦”。
我还没清醒,随口问道:“拣的?”。还没有反应。
“走廊上拣的。”
原来,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都没有想到这是个好的开始。
找了个车,沿色达方向走。希望可以搭上色达的本地车,这样今天就可以赶到佛学院。正如LK说的,如果捡到三十元钱还不算好运的话,那么,搭上色达的沙丁鱼车,应该是好运气吧。司机是色达的,一路拣客一路放客,我也坐出了有史以来最高的记录,一个长安之星塞了11个人,有个喇嘛还是用站的哦。神奇吧。
我们象沙丁鱼挤在罐头里一样。快乐的看着窗外和车内的风景。心情好极了。彼此都搭上了车,没有搭错车,看上去每张面容都很满足。
坐了6个小时,解放了我们的屁股。佛学院路口。小饭馆一人吃了碗小面,因为没有馄饨了。基本上可以说不好吃。好在都是烂中极品,饿了啥都吃。
佛学院。原本想找一个在那里出家的朋友,和登记处的人打听,那人死贫:“这里找人啊,很难啊。这里太大了。和在成都找人一样,很难找的哦。你出钱嘛,三天之内可以给你找到。”(妈的,又谈钱,不找了不行啊)。
登记完证件,上车走人(佛学院门口的班车¥5/人)。佛学院在海拔约3800米的喇荣山谷。车到了山坳就不肯再上山,除非¥30/人。(妈的,又谈钱。日。)想都没想,自己赚这30元吧,仨背着大包朝山顶走去,估计都先咽了口口水。很具体的一段路。海拔不低,估计再一个来回我们都得挂了。到了山顶,卸下包,一屁股坐在招待所的台阶上,说什么也别叫我去看房间。谁叫跟谁急。烂克很懂事,乖乖上楼打探,我们也很快就摸清了大致情况。这里只有一个饭店,叫“和平饭店”。只有一个招待所(¥10/人),仨人没有异议的称之为“新龙门客栈”。
一切的一切,从这一刻开始展开了。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那只羊每天都在2楼的楼梯上不动声色,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它还在。那木头地板和不隔音的墙斑驳不堪,阳光斜刺里透过窗户,坐在床上,窗外就是风景。眼前大片的僧房,大片的绛红飘飘,大片的云朵挂着,大只大只的乌鸦飞过。视界里的一切景象,热烈的展开,拉远。整整一个山头的经幡也热辣辣的飞舞。
人声热烈,梵音似乐,都在身外。此刻的内心,寂静无比。一切退后。
转坛城。
实实在在的转了6圈。碰了2次脑门儿,眼花缭乱的。心想,这也许是咱定数不够,叫咱要用心呢,接下来就很仔细的念着6字真言,一老者跟在身后,笑眯眯的越过我,用不是很清晰的藏式汉语问我懂得念嘛?仔细的听了听,方才醒悟,忙的瑟的说:“会。嗡玛尼呗咪哞”。老者点了点头,俺就更得意了。
“还有一句呢?”
“啥?还有一句?”
看我一脸迷茫,老者舌头一抡,跟音乐似的发音。顿时就脸红脖子粗的。没明白啊。看我这样,老者很有耐心的有念了一遍,我感觉我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发音上,其他的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接下来的几圈我就2句抡着念,感觉要念成紧箍咒了,就这样撞了2次梁,这咒到底是戴上了。
转完坛城,照片没拍几张,数码相机捏了一手的汗。也就这相机没顾的上掩藏好,工作组的摔哥把我拦下来,示意检查相机。叫我删了2张全景,还交代说登个记。
“俺没身份证”
“其他的证件也行”
“学生证行不”
“可以。我们就是做个记录。这些照片不要随便发到网上哦。还有什么空间啊这些的。”
“啊。”感情都知道啊。那您知道俺都不用真名的么。
过了几天清修般的生活。照例上和平饭店吃饭,那里解决1餐,然后揣几张大饼回来,饿的时候垫巴垫巴。上山的时候就啃压缩饼干,下山了就杀到和平饭店。可怜啊啃了2天的大饼的仨烂人终于决定在这一天顿吃米了。
“对不起”,小哥说:“没有米饭了”。最后啃的是馒头。妈的,其实不如啃大饼。
招待所没有用水的地方,烂人们有了懒惰的借口。没水嘛,脏就脏点喽,省得每天洗了擦擦了洗的。热水也要3元1瓶。当然这钱能省也得省了,去楼梯头的阿爸阿妈屋里噌。也不算白噌啦,给他家小孙孙带几只铅笔和几块橡皮,好歹读书了嘛,用的上。算是心理交换吧。其实大家都不容易。
晚上睡下以后,耗子就开始在顶上跑来跑去的,一直得跑到天亮。也没听烂人谁抱怨,估计不是没听见就是已经习惯。不就耗子嘛。不知道这地方能生活的好嘛。都不容易啊。
五明的夜景真是很美。夜空下僧房的灯昏黄点点,夜空的灯银色闪闪,入厕出来站在高处向下望,忍不住就想烂吼几声。空气象从冰箱里冻过,清冽透彻。月亮在云后,小路在星光下泛着白光,这漫天的星光已经是记忆里深刻的一刀。
呵。回忆真是有点不堪。
起风了,风在走廊里穿来穿去,发出声响,和着山坳里的各种微妙的声音。会忘记身在何处。只是一转头看见身边2张熟悉的面孔。温暖塌实。
睁开眼睛。早上6点。窗外白茫茫一片。一夜雪覆。视线所及,只有白色。
等俺狂呼烂吼一通,俩烂人居然不甩老子,继续当猪。妈的。昨天还在说要是有场雨会比较不一样。没想到上天给了一场大雪。
这场雪,让我们无法言语。唯一能做的就是灭山行动。象孩子一样激动万分,爽的神经膨胀。水墨画展开在眼前,僧舍象黑色的旗子嵌在白皑皑的山坡上。忍不住的仰天大笑。谢谢,谢谢上帝,谢谢阿拉,谢谢菩萨,您对我们真是太厚道了。
太阳出来了,烤着俺眼晕出汗,下山的路滑的不行了,俺平衡系统一定是出了问题,怎么会十步一摔呢,摔的俺呲牙咧嘴,屁股疼了,手臂也拧了。
摔的俺看见山路向下就心理障碍,那俩烂人笑的都快岔气儿了,怒。
最后都不忍心再听俺一声声的惨叫了,才向俺伸出友谊之手,呸。
来色达之前。缺乏想象。大抵和所有的高原一样,快乐高反之地。但是它,却用它的方式展开了自己。很意外也很惊喜。就象那只拖拉机,它存在就是让我们在阳光下可以睡觉,可以什么也不说的在这方蓝天下恍惚着一切美妙的时光。流云。风沙。身影和目光。
回程的16个小时,差不多睡去了全部。记忆中的长途车外的风景,就算睡着也能感觉到一直就在风景里。
就象,就象我们只是约在宽巷子喝了杯茶,就象我们只是在李姨门外的大树下有一句的没一句的耗掉了一个下午的光阴,就象不知不觉的,睡了一个舒服的觉。

寂静的是空山上的呼吸
寂静的那片白雪下的灌木以及阳光中的风马旗
寂静的是清晨的念语
寂静的是那大片大片的僧房以及大片大片的绛红
抵达
如同穿越梦境的飞翔
趋于光的需要
穿过深蓝
这不着边际的寂静
穿越时间 到世界的尽头去
而过程 也许是一生也许是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