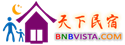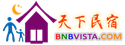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这里的阳光是跳跃的,这或许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特点。尤其在靛蓝而辽阔的夏季,那阳光明媚又调皮地跃上我的发稍,吻着我的脸颊,跳在我的掌心,如此热情又多情地拥我入怀。我的皮肤被灼得微微发红,我被一种疼痛得幸福裹得很紧,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一片我向往已久的土地,现在我真的可以面对它了。
博乐的火车站很小,和甘肃的柳园站有点相似,可是因为没有敦煌的名气,远远不如柳园站热闹。车站前一个平台,横七竖八的停了些中巴车,皮肤黝黑的汉子或女人扯着沙哑的喉咙拉出站的客人上车。
我们看见了来接站的朋友,直接上了一辆白色的依维柯,车箱里咝咝冒着冷气,和燥热的外面犹如隔季的两个世界,为我们消去大半的暑气。
从博乐火车站到博乐市大约45公里,车要走一个多小时。据说,当初火车站要修在市区,可是为了地盘之争,博乐的决策人竟然不同意,因此修在了45公里之外的荒戈壁滩,当时的鼠目寸光为人们造成了许多不便,不过,这倒为我提供了一个有外及内认识博乐的好机会。(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当你遇见麻烦的时候,要想办法把麻烦转化为快乐:)
我把头靠在窗玻璃上,不错眼珠的看着窗外的景色,手轻轻拍着自己的腿,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脚已经浮肿了,原先松松的系带凉鞋被撑的满满的,但我来不及抱怨,捕捉着每一幕转瞬即逝的景色。
这里除了戈壁还是戈壁,远方的山隐在白色的热气中,近处是丛丛蓬蓬茂密生长的杂草,给单调的黄色添了不少盎然的生机。几乎看不见人烟,偶尔有几只羊冲上马路,司机一摁喇叭,它们便惊慌的四散逃开去了。
在我开始觉得长路迢迢不知尽头的时候,路旁出现了高耸的白杨,叶片被风吹着,被阳光映着,好象一只只银色的小手掌,树后掩着稀稀落落的人家。这已是城郊了,不一会儿,一个藏在戈壁深处的小城便跃入视野。
博乐给我的感觉是清新又羞涩,街道宽阔又洁净,人少而悠闲。他们三三两两的在路旁的绿化带遛弯。博乐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唯一的市,常住人口七万左右。猛一听七万人还是蛮多,细一想我们院儿住的人都有三万,这才觉得这个小城市实在很秀气。
傍晚,我们下榻在博州宾馆,热情的东道主要为我们接风洗尘,为我们送上下马酒。这下马酒是蒙古族的礼节,意为远方的客人风尘仆仆骑马而来,只有喝了下马酒才能下马,听上去蛮有意思,当时我还好奇的傻笑呢,但真正领教了下马酒威力的人就会叫苦不迭了。
桌上的饭菜很丰盛,熏马肠,风味羊排,糊辣羊蹄,手抓肉,薄皮包子,烤羊肉串,盖饼,馕包肉……全是极有民族风味和特色的小吃。主人可不答应这么快就转入正题开吃,而是一杯杯的敬着认识酒,下马酒……大家可千万不要以为是用普通秀气的小酒杯盛酒,一上桌,豪爽的主人大手一挥,小杯全撤下去了,换上了一只只敞口的茶碗,一瓶博尔塔拉本地产的烈性酒顶多四碗就倒完了,看的我是心惊肉跳,这饮酒可不是啜饮,而是真正的豪饮,牛饮。眼一闭,手一抬,一碗酒便咕咚咕咚倒进喉咙里去,比喝白开水还要利索呢。
看着那一只只斟满了白酒的大碗,我已经预感到了不妙,提前申请喝“金可乐”,这金可乐是博州的特产,色泽同可口可乐差不多,入口爽滑,回味悠长,唇齿间徘徊的是一股淡淡的中草药香味,味道挺独特的。
这么几圈下来,他们的人马面不改色,我们的人已经面红耳赤,说话也磕磕绊绊的。最后任凭他们怎么威胁恫吓,我们的人都是一副“咬住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凛然的样子。
主人自有绝招,从门外唤来两个蒙古女子,说是要以歌酒的形式为大家助兴。大家不知是计,纷纷拍手叫好。那蒙古女子脸如满月,细长的眼睛,高高的颧骨,薄薄的嘴唇,不是那种令人一见,心怦然一动的美丽,但有一种冷傲的个性美。
初一看蒙古姑娘要唱歌,我也是暗自得意高兴,居然有这等美事,听着那么动人的歌儿,吃着美味的饭儿,还有献上表演的可人儿,人生快意之事,莫过于此了吧。殊不知,天下没有免费吃的午餐,天下也同样不可能有没代价的听美女唱歌。
所谓歌酒,就是一歌一酒,相互搭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听了人家的歌儿,就得喝人家的酒,这规矩马虎不得,想赖皮那是万万不能连门儿也没有。
只见那两个婀娜的女子已经从首席开始敬酒了。一个女子将酒缓缓倒入金碗中,透明的液体顿时流光溢彩起来,手持酒杯的女子便开始高歌,那声音高亢明亮,婉转悠扬,凭我这个才疏学浅的小女子之笔力已无法形容,在此斗胆借刘鄂《老残游记》中《历山山下古帝遗踪,明湖湖边美人绝调》一节的片段,以弥此憾,绝对恰如其分,无丝毫夸张。
那歌声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服帖;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处不畅快。越唱越高之处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丝钢丝抛入天际,哪知她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峭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西面,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待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
就是这样奇,不亲身体会很难想象出这些从小在草原上练的歌喉是多么嘹亮醉人,在这歌声中,你不知不觉融化在蒙古女子左右顾盼的含情秋波里,不知不觉接过了酒杯。喝这酒也有讲究,先将中指蘸入碗中,向上弹一下,再向下弹一下,接着抿一口,然后递回去,那蒙古女子垂着眼睑接过来,假意放唇边做一个喝的姿势,然后一弓膝盖,又回递过去,这时的你就得一饮而尽了,然后倒扣碗,表示酒干碗净,蒙古女子将搭在腕上的哈达挂上客人脖子的时候,客人表示感谢,蒙古女子的歌声这才恰倒好处的戛然而止。
这献歌也颇有讲究,她们会察言观色,为每个人选的歌都不同。为长者献上表示敬重的歌,为远方的人献上欢迎歌,为年轻的小伙子献上情谊绵绵的好哥哥歌,为姑娘献上姐妹歌,……她们可以一首歌不重的为每个人准备不同的歌。总之,大家在歌声中好象被施了魔咒,心甘情愿的接过金碗,一饮而尽了。
一圈十几个人挨个献过来,蒙古女子的嗓音依旧清澈透亮,没有留下丝毫疲惫的痕迹。我们的人原想喝了不必再喝,大胆的要求蒙古女子唱个蒙古长调和腾格尔的《蒙古人》,那女子依旧笑意盈盈的边唱边递过酒来,愁的提议之人悔不该当初,恨不能嚼碎牙齿咽进肚子里。但歌要听,酒要喝,又是大碗大碗咕咚咕咚的下肚了。
蒙古女子将腾格尔的《蒙古人》演绎的别有一番滋味,少了深邃苍凉刚硬,多了柔情温和妩媚,想必这余音绕梁,恐三日难绝吧。我已经不敢再听下去,这代价未免太惨重了,拉过邻座从北京来的女孩子,找了个借口,溜之大吉也。
那人仰马翻的一桌子人;觥筹交错满屋灯火;或缓或急,忽高忽低,百变不穷的歌声,统统被我们丢在身后,我想让博乐的夜风清凉我被酒香熏得酡红的脸庞。
我俩手拉手走在街边的路灯下,迎面而来的人走过我们还要回头张望一下,那可不是因为我们有倾国倾城的美貌,而是因为我们的脖子上傻呼呼的围着长长的哈达。我们一会儿扮热血沸腾的五四青年,将哈达象围巾一样绕在脖子上;一会儿扮演咿咿呀呀的戏子,翘着兰花指,挑着哈达一端哼着;一会儿扮演黑白双煞(她着黑衣,我穿白衣)的侠女,挥舞着哈达……
我们就这样在这个小小的城市中,穿越寂寞冷清无人的街道,穿越灯火辉煌热气腾腾四处飘着小吃香味的夜市,一切恍如梦中,可又真实的可以摸得着,嗅得见。我们互相笑着,闹着,搂抱着,大声歌唱着,肆意的放纵着,快乐的疯狂着,孤零零的星悬在天空,温柔清寒的月光洒向人间,我们甜蜜地绽放唇边那朵小小的微笑,我想,我们大概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