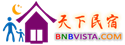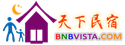2003年上半学期,我正值青葱岁月的尾巴,和所有小屁孩子一样被学校禁锢着天高地厚的所谓激情和梦想。它们像武侠小说里描述的真气一样在体内乱窜, 最终仅仅是滋生了一脸过剩的油光和青春痘。还有一点私房钱,一千出头,准备用来去西藏的。那是一个从高中时就开始孕育的念想,然后一点一点的存,打算存够 了两千就出发。
相信那一年大部分的在校学生都深深地感激非典,使他们的暑假足足提前了至少一个月。我却在学校宽容的默许师生本是同林鸟大难临 头各自飞的时候做出了一个理智却不明智的决定:留校。结果这两个月的有期徒刑把我关得几乎发疯,足不出户的反作用就是离开,远远的离开。去西藏,钱还没有 存够。封校解禁第一天,我带上这些钱,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厦门旅游手册,决定去看海。
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看着窗外,也就这样过去了。后来有朋 友质疑我坐火车从来只坐硬座的行为。是的,我不至于没有坐卧铺的钱,但是在车厢里,看着与我年纪相仿甚至比我还小的女孩子,在底层看着城市绚烂的梦想的女 孩子,为了省钱从一个站台站到另一个站台,在促狭的过道里被挤来挤去,而我不过是出门旅游。不为病痛,不为极度的疲劳,舒适的躺在卧铺上,是一种原罪。只 是我的想法,而已。
坐我对面的伯伯,长了一张和善的豌豆脸,白天的时候一直找我讲话,满脸和蔼。可惜他说什么真是一个字也听不懂,问他能不能 说普通话,他继续吐出一串天书,我只好堆起微笑并适时辅以点头。后来在江西的一个小站,豌豆伯伯终于下车了,矮胖的身子吃力地从座位下面拖出他的蛇皮袋 子,又爬上座位从行李架上拽出好些塑料袋,大包小包的扛在身上,回头对着我咧嘴笑了一下,就消失在同样等着下车的人流中。我松了一口气,揉揉快僵掉的脸。 他是谁?他要去向哪里?车厢里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在乎,这个小小的人物,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倾诉意愿,对着一个根本听不懂他说话的陌生人不停的诉 说?这个站台,他是抵达,还是出发?这些都如同他对我说话的内容一样,永远都不会得到解答。我一厢情愿的希望,他是打工回来,门口有翘首的妻儿,在等待着 他和他带回的积蓄,桌上有熟悉的菜肴,在迎接主人的返家。
进入福建境内,火车明显的放慢了速度,之前在华北平原上笔直奔驰的列车此时仿佛一条 温柔的蛇,缓缓地沿着闽江蜿蜒着,经常能够看见转弯时的火车头又在转向另一个方向。窗外的江水碧绿柔和,草叶尖儿擦着车窗掠过,再加上那不紧不慢的哐 当……哐当……,使人忘记自己是坐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冰冷的载人工具里,而生出是乘坐一列观光小火车的错觉。
车近厦门,广播里开始播放闽南歌曲,我对面的两个人大的学生也一脸开心的边收拾东西边跟着唱,还很热心的教我唱,说是为了熟悉闽南话-_-!~~(可惜我现在只记得一句“挖虾米”了,哦,还有“爱pia掐嘿牙”)
晚上9点多,我背着大书包站在了厦门的街道上。这就是厦门?我打量着,在夜色里,它和其他的城市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躲在夜色后面的高楼,宽敞的 马路,幻彩的霓虹灯,一样的巨幅广告牌上模特儿还是摆出一样诱惑的姿势。找到住处,又发现原来以为带的洗发水结果是护发素,凑合着拿香皂洗了头,倒在床 上,一夜无梦。
第二天,去植物园。喜欢植物,安静,温暖。动物园让人太伤感了。走在街道上,才一点一点觉出与北方的不同来,街道非常的干净, 而路边的道旁树,之前没有注意,后来发现居然是芒果!芒果!天啊~~上面还有绿色的果子呢,拿芒果来做道旁树,简直太奢侈了!公共汽车行驶在弯弯曲曲的街 道上,耀眼的阳光照得人几乎睁不开眼,原来南方的海边,并不总是水气氤氲的。
万石植物园,其实是半座山,还有半座,划给了南普陀寺。爬到山顶,有个小门,要去到另一边,就再掏一次门票钱,合作默契,心照不宣。
有很多植物,没有很多人,我开心得在植物园里逛了几乎一整天。那里的植物,大部分都是“放养”的,人工的痕迹被降到最低,区别于北京植物园的严肃呆板。 一些漂亮的温室零星散布,保护着那些本不属于这个环境的植物们。偌大的多肉植物的温室里,只有我一个游客,拉着管理员问这问那,他似乎也挺高兴有这么一个 人对他研究的东西感兴趣。两个人头并头,从门纲目科属说起,再到各自的产地,习性,特征,不同植物之间的相互比较。先生不拿讲鞭,不写板书,没有课后作业 和期末考试,时光流转,我快乐的作着学生。
晚上去了中山路,两旁的西式骑楼给中间留出一条狭窄的路来,路边有很大的屈臣氏,还有巴黎春天,婉 转旖旎,温习着旧日浮华的气氛。在光合作用书房里流连了一会儿,等朋友来把我领走。然后我们去了一家据说很有名的冰淇淋店吃刨冰,墙上给涂满了文字和图 画。一点一点地将别人的心情看将过来,那碗加了生鸡蛋的刨冰也就不知不觉地吃下去了。顺着中山路走下去,就是海。夜晚的海边人头济济,看着对面鼓浪屿明如 白昼的映在海面上,空气中一浪一浪打来水的腥气,与内陆江河的气味似乎并无二致。这就是海么?漂浮着五颜六色灯光的水面,默不作声。
早上睡到自然醒,盯着雪白的天花板,阳光晒到脚趾头了。动动金色的脚趾,起床吧,今天去鼓浪屿。
推托掉码头密密麻麻的导游,自己抬脚乱走。看见新华书店,拐进去,换了一张牛皮纸的鼓浪屿地图出来,再照着地图乱走。深院高墙,逼出窄窄的巷子,曾经的 衣香鬓影,明争暗斗都作尘散,只剩了那些闽式法式美式哥特式的建筑,在无人听见的夜里闲坐说玄宗。在一个寂静的院落靠着紧锁的门前高大的廊柱坐下,院里的 树木已高可参天,落叶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盛夏的风吹过,地上和树上的叶子一起簌簌作响,好不热闹。三一堂上着锁,墙上写着主是好牧人,潜台词不知是不 是非羔羊莫入。天主堂的门是敞开的,洁白的耶稣像在阳光下张开手臂,我坐在后院的长椅上接电话,贴墙有棵树,上面结着青色的木瓜。
终于走到接 近外海的那一边,很大、很大一片蔚蓝的水,无边无际,间或有小块的礁石和远处的岛屿点缀,金色的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我看得有点呆了,慢 慢走近海滩,脱下鞋子,看着无色的水浸上脚面,又迅速退去。还是不敢相信这就是海,心里在想,游泳池的人工海浪,也是这样的。然后伸手捧了一捧水送入嘴 里,#¥%$—&……终于信了……>_<
我喜欢鼓浪屿的另一点,是据说舒婷仍然住在这个小岛上。海子死了,顾城可耻的死了,但舒婷完成了她作为诗人的使命后,继续活下来,和我们一起。我没有去看她到底长得什么样,只是保持每一个与我擦肩而过的普通中年妇女都有可能是她的想法,就很好。
手绘地图终究不够精准,于是有了我在岛上的唯一一次迷路。我本来是要往本岛方向走的,但却走到外海边去了,前面是一道丫字形岔口,四顾无人,除了一个老爷爷在岔口边的小卖部外晒太阳。我走过去:“您好,请问XX路是前面往左拐还是往右拐啊?”
老爷爷笑眯眯的看着我:“@#$%^&*…#¥?*&^%$#”
。。。。。。(@_@啊?什么?)我硬着头皮:“不好意思,我听不懂闽南语,您能讲普通话吗?”
老爷爷继续一脸天真无辜的看着我:“@#$%^&*…#¥?*&^%$#…………”
我既不能说“挖虾米”,也不能说“爱pia掐嘿牙”。火车上的人大同学,你们当初为什么不教我“实用闽南语900句”?!
于是我回报以灿烂的微笑:“嗯,好的,谢谢您了。”,然后180度转身,原路返回。
原路也不再是原路,来时空旷的路口,回去却看见停一辆小推车,上面挂了“叶氏麻糬”的牌子,还有各式执照奖牌,牛气烘烘。车后站着夫妻二人,老婆矮胖, 老公高瘦,相得益彰。两人都全无生意人的笑脸,主攻做麻糬的老公由于目标显眼,更显得一脸紧张兮兮的凶相。不过麻糬好吃,热热甜甜糯糯。虽然有点奇怪,还 是想起了北京,MJ的脸在眼前晃:“丫头,去厦门,一定要去吃mua(三声)吉!”
那时候去鼓浪屿,还是不要钱的,但是离开鼓浪屿却要买船票。最后一次回本岛的时候,我买多一张船票,留起来,可是终在数年之后和笔袋芝麻一起丢失了。连想象中对着一个帅哥故作深沉的搭讪:“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这样的庸俗桥段也再无法上演。
晚上在厦门大桥下面晃着脚丫乘凉,一颗颗黄色的灯光倒映在漆黑的海面上,无比华丽。
之后去黄厝游泳,去鳌园,去爬普陀寺然后下来在放生池边喂鱼喂乌龟,在集美大学的屋顶看夕阳西下,白鹭归巢,在厦门大学湖中心的小岛上打盹(那个湖叫芙 蓉湖,上面有个女生的雕像,数年之后,那个可怜的女生被呼为芙蓉姐姐:P)。每天下午,看小商铺门前一排排开雷打不动的功夫茶,时间就这样的,慢慢流过, 并依然流淌在我现时的梦里。